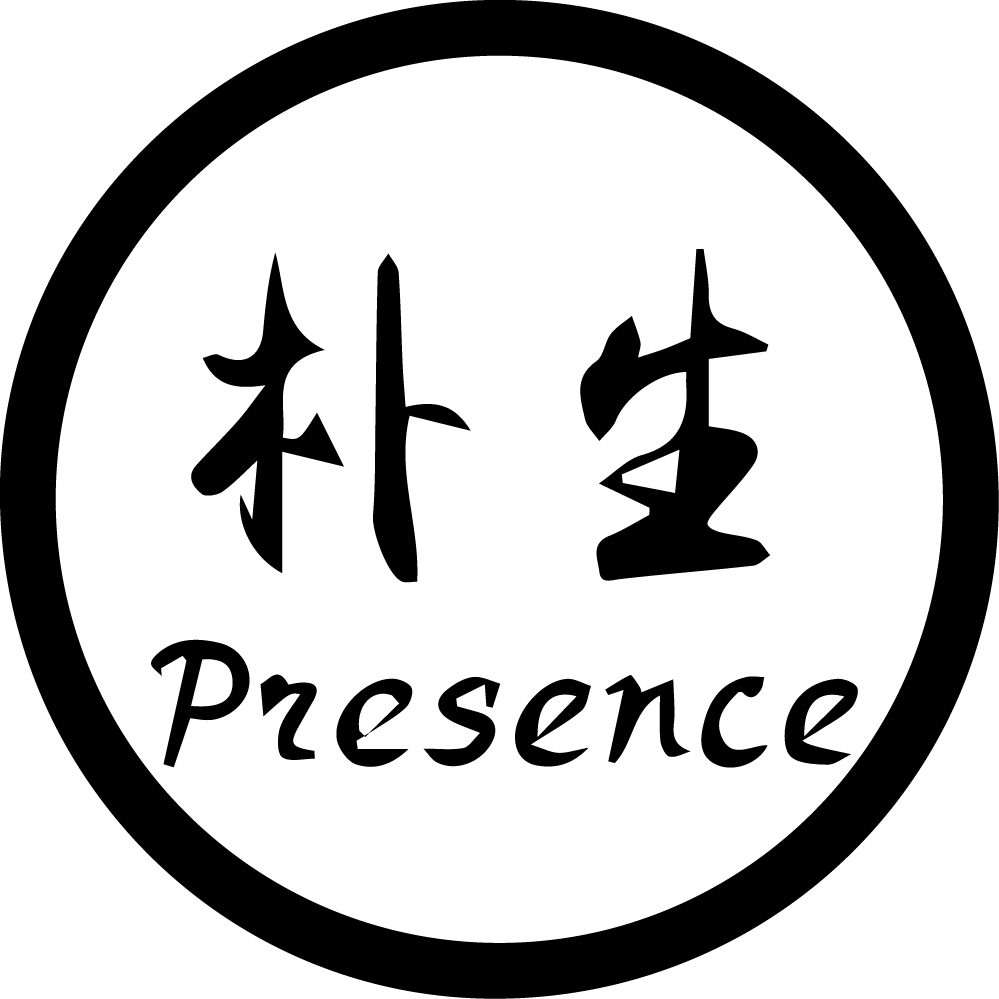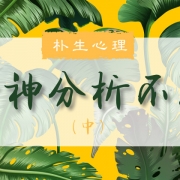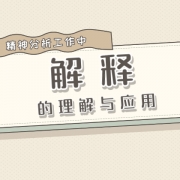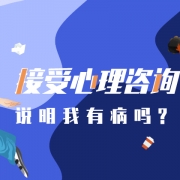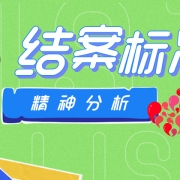自杀/自伤行为的心理动力学理解

自杀/自伤行为的心理动力学理解
在我们的临床心理工作中,个案自杀或自伤行为是一类比较难处理的行为。自杀的行为动机复杂难辨,而且自杀很可能具有初级和次级获益,如果放在家庭系统、组织系统甚至是文化背景中,自杀行为的理解就更复杂了。
虽然许多精神疾病最终都可能以自杀的悲剧来收场,不过一般说来,和自杀、自伤行为关联最为密切的一类心理或精神疾患还是情感性疾患(affective disorder),如重度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
首先,带来自杀这个行为的因素有很多,至少要涵盖了生物的和心理的两大维度。临床心理咨询中所点滴累积的心理动力学观点,就病因学上来说,或许是神经化学因素的次发现象。因此除了心理咨询和治疗取向上的尝试,各种生物性(或化学性的,比如药物治疗)的治疗方法也要积极运用。因为对许多个案来说,仅仅只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恐怕是不够的。
在一个对比疗效的研究中( Lesse,1978),单纯只接受心理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其治疗反应率低到只有16%;反之同时接受药物治疗和电痉挛治疗的患者,结果分别是83%与86%。
拯救个案的性命远比死抱着单一的治疗取向或者是一味地维护正宗的理论要来得重要。不管是自杀或自伤的行为或观念,还是我们心中的各种思想或行为模式,其实都是遵循多元交互决定(over-determination)的原则,是受诸多因素在非线性、混沌、复杂的交互机制下影响的。
自杀的动机极其复杂而多元,而且往往模糊难以辨识( Meissner,1986)。因此临床工作者必须要仔细倾听每个个案所说的话,特别留意其中的移情——反移情发展,最后才能推敲出埋藏其中的动力内涵。
弗洛伊德(1917/1963)对自杀所作的精神动力学诠释跟他抑郁症的理论息息相关。他假定,自我只有在把自己当作客体的情况下才能够杀死自己,所以他假设自杀是一种被置换的谋杀。也就是说,意图毁灭内在客体的欲望被导引向了自身。后来发展出结构模式之后( Freud1923/1961),弗洛伊德修正了其原有的理论,认为自杀是施虐超我的部分对自我的加害的见诸行动。
卡尔・门宁格( Karl Menninger,1933)对于自杀的看法则比较复杂。他认为自杀行动的背后至少有三个欲望作为其主要动机,分别是想要杀人、想要被杀以及想要死的希望。
其中,杀人的欲望并不只是针对内在客体而已。往过的诸多临床经验反复证实,自杀往往是为了要摧毁存活者的生活。
对很多个案来说,自杀是唯一能够满足复仇欲望的手段。比如,我们可能会发现,在一个家庭中,太太往往会通过自伤或者自杀的行为来达到报复那个“负心汉”的目的;在自杀个案的客体系中,残酷的虐待者与被凌虐的受害者是不断断重复上演的戏码。其内在客体不断地进行迫害,使个案陷入修境;反过来说,假使个案认同了这个加害者的意象,他便可能转而折磨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在某些案例中,个案可能会以为,唯有透过自杀而臣服于加害者方能终结这出闹剧( Meissner,1986)。曾经有人把样的内在客体意象比喻为“隐匿的刽子手”(Asch,1980)。
在某些案例身上,攻击性在自杀动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一定那么的明显。费尼切尔( Fenichel,1945)曾经提出,自杀可能是为了要实现一种再团聚( reunion)的欲望:个案可能满怀欣喜地想要和丧失的所爱或客体得以奇迹般地重逢,或者是要和那个慈爱的超我形象作自恋式的融合( narcissistic union);客体的丧失(loss of object)往往是自杀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动力学原因,许多个案都透露出对丧失客体的依赖与怀念( Dorpat,1973)。
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自杀也可以是一种退行性欲望,自杀者期望跟丧失的母体重聚。1978年由琼斯教士( Reverend Jim Jones)所带领的一起发生于圭亚那( Guyana)的集体自杀事件中,他开枪击中自己头部之前吐出的最后几个字便是“妈妈………妈妈…”。
在自杀行为中常常常包含病理性的哀悼(pathological grief),特别是在自杀行为发生在亲密他者的忌日或其他重要时间的时候。众多研究已经证实,自杀行为与父母亲忌日间的关联具有统计上的意义( Bunch and Barraclough,1971)。
另外,当个人的自尊和自我统整性( self-integrity)都必须要依赖于丧失客体之间的依恋关系时,除了自杀,恐怕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恢复自我的统整性了。这便是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治疗理论中所论述的那种敏感、脆弱的自体在缺乏镜足够的映或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功能支持下而崩解以至于自毁的行为。
一则临床案例
他们发现有七个因子可以用来预测一年内的自杀危险性,分别是:恐慌发作、精神焦虑、严重丧失乐趣与兴趣、酒精滥用、专注力下降、、失眠以及抑郁情绪的困扰。
比方说很快速地由焦虑转为抑郁,再从焦虑转为愤怒等长期的预测因子则有:无望感、自杀意念、自杀意闻以及过去的自杀史。
许多研究都发现,无望感是一个很好的预测因子,甚至比忧郁因子的预测力还要高。这里所指的无望感可能和种偏执、僵化的自我评价有关:尽管一再失望,也无法转变。如果一个人无法达到对自我的严格期望,无望感便随之而生,自杀也许就成为唯一的出路。
艾瑞堤(1977)曾经提过类似的说法,如果个案没有办法改变支配自己的观点,或者改变自己对支配性他者的期待,那自杀的危险性便会升高;同理,如果个案的自杀意念是自我协调一致的(ego- syntonic)换句话说,他可能觉得自杀没什麽不好的,甚至早已放弃与自杀念头挣扎或抵抗的时候,此时的危险性也会升高。
要从精神动力学的观点来探讨自杀和自伤行为,临床工作者必须了解促发事件的本质、意识与无意识中的动机、以及其他原先已存在的心理影响因子;如果要是将自杀行为放在家庭系统、组织系统甚至是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对自杀行为的理解就更复杂了。
已经有研究者( Smith,1983; Smith and Eyman,1988)使用投射心理测验( projective psychological tests)区出四种不同类型的自我功能与内在客体关系,以此来作为预测自杀危险性的参考。
其中自杀危险性最高者的特征包括:存在偏执、顽固的被哺育的幼儿式幻想,同时又无法直接了当地表达出依赖的需求,因而产生自我矛盾;对死亡抱有一种当真但又矛盾的心态;过高的自我期待;对于情绪的过度控制,尤其是对攻击性的压抑。
尽管上述模型比较适用于男性个案( Smith and Eyman1988),但对攻击性采取过度控制的态度这一点,仍可以有助于辨识出有高度自杀危险的女性。
上面这些测验的结果告诉我们,有些原先就已经存在的、倾向于自杀的心理结构比某个特定自杀行为背后林林总总的动机要来得更具一致性。
– THE END –
(本文内容为厦门朴生心理原创,版权归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所有。
转载请联系15859242450,并注明出处。)
预约咨询请添加助理微信

编辑: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