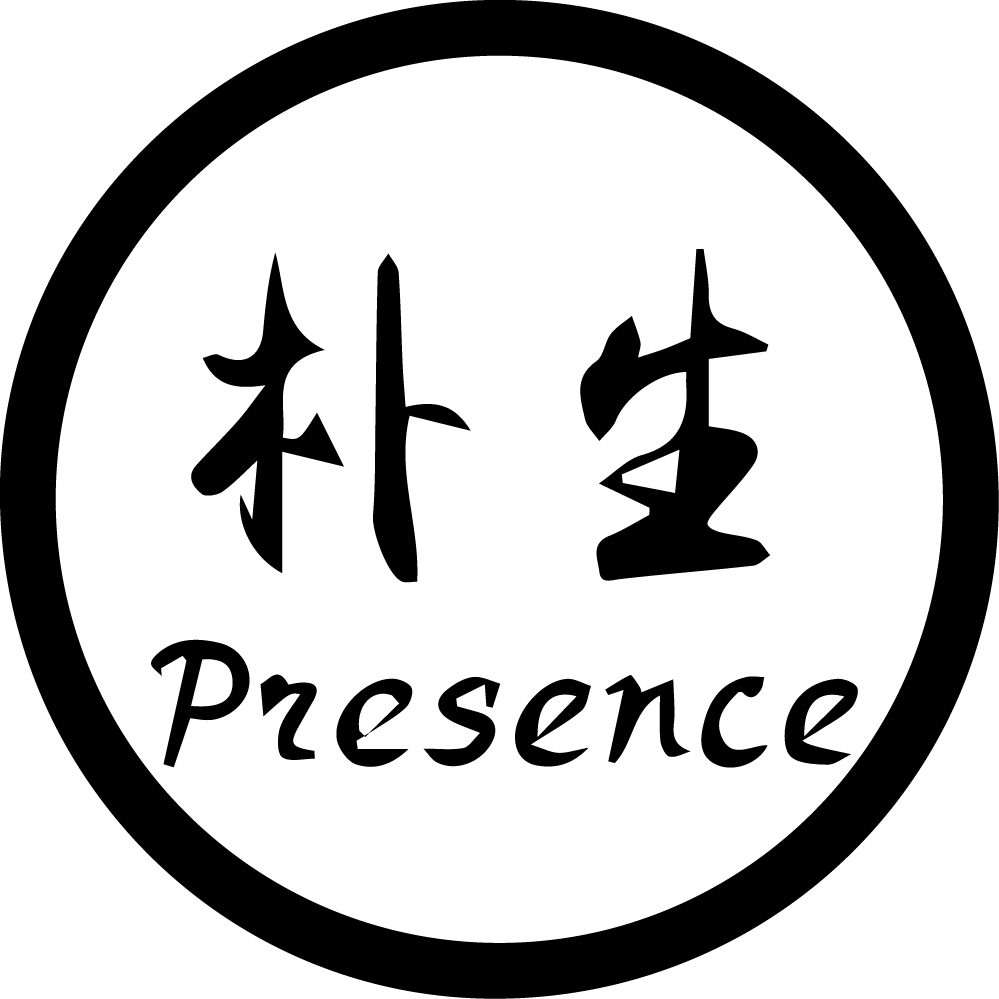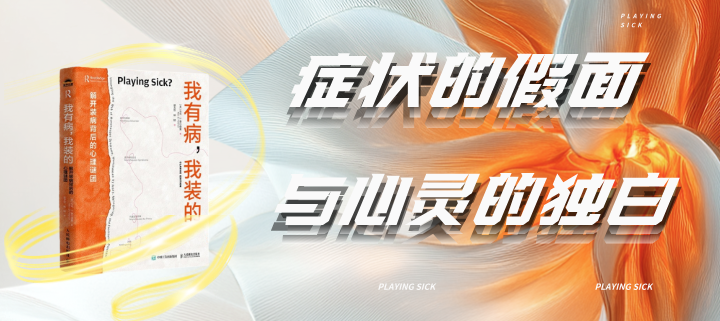《我有病,我装的》译者导读:揭开装病的谜团,症状的假面与心灵的独白
原创: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
装病,这一行为常被视为道德瑕疵或人格缺陷,却鲜少有人追问:为何有人甘愿以疾病为茧,将自己与世界隔绝?从表面看,这是欺骗与操纵的戏剧;深入内核,却是人类心灵在绝望中叩问存在的悲歌。当代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双重视角:前者揭示了个体如何通过“自体客体”的缺失构建病态防御,后者则直指装病者对自由与责任的逃避。正如萨特所言:“地狱即是他人。”而装病者或许正试图以谎言为盾,抵御他人目光中的地狱,却在不自觉中将自己困入更深的牢笼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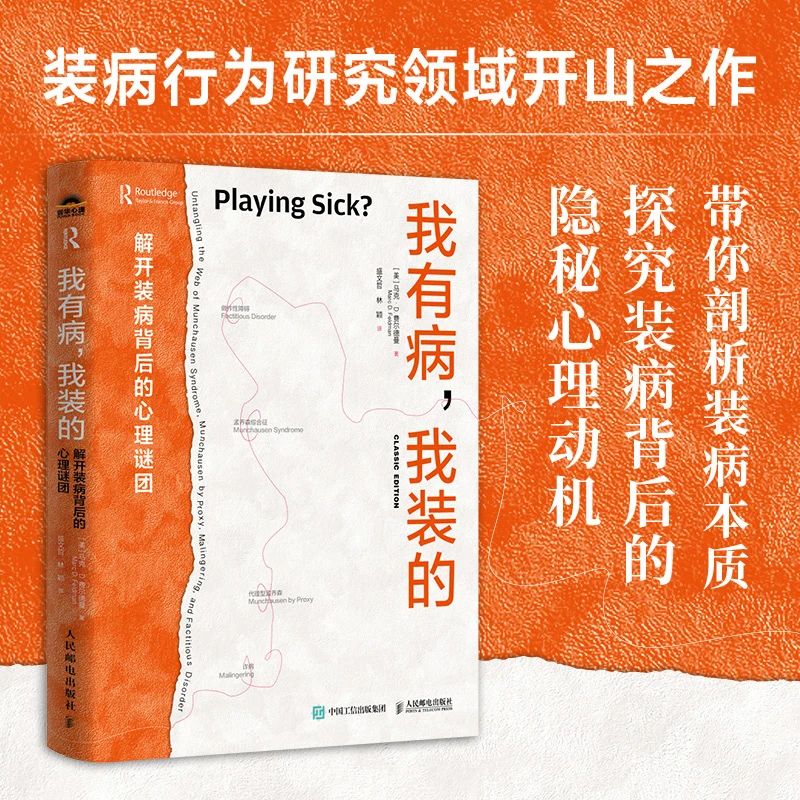
谎言施虐的戏剧与权力的幻象
破碎自体与反向操控
装病者如同提线木偶师,将他人化为傀儡,线绳是精心编织的症状,舞台则是医患关系或亲密纽带。每一场“疾病表演”,都是对早年失控体验的报复性改写。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家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的曾指出,当个体早年未能获得足够的“自体客体”回应(如父母的共情与肯定),其自体结构会陷入脆弱与分裂。装病者的攻击性谎言,实则是通过操控他人来弥补这种断裂。例如《我有病,我装的:解开装病背后的心理谜团》这本书案例故事中的德里克,他长达两年对未婚妻的欺骗,不仅是一场施虐的狂欢,更是试图通过“逆转创伤”重建自体完整性的歇斯底里——他需要看到他人的无力与挫败,以此确认自己并非全然被动。
自欺与权力意志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那本《存在与虚无》中提出“自欺”(mauvaise foi),即人会通过否认自由本质来逃避责任。装病者的施虐行为,本质是权力意志的扭曲表达——他们以疾病为武器,将自身置于“必然性”的庇护下(“我有病,所以我必须得到照顾”),从而规避选择的焦虑。尼采曾说:“权力意志是生命的基本冲动。”那些装病患者却将这一冲动异化为对他人的支配,正如故事中一位主人公梅丽萨极度渴求通过她自己的智力来碾压医生获得快感,实则是在用虚假的“疾病权威”填补内心的虚无。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了另一位案例主人公戴尔德丽的无意识报复,她既是向父母强加生活的反抗,也是存在性绝望的具象化表达。她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疾病“无法治愈”俨然是存在主义口号的大声疾呼:若世界拒绝赋予意义,我便以疾病为旗帜,宣告自我的荒诞主权。
脆弱的茧房与共情的呼救
镜映缺失与症状防御
精神分析师科胡特强调,人类心灵健康自体的发展依赖于“镜映自体客体”的回应——即来自他人对个体存在、情感、价值的确认。《我有病,我装的:解开装病背后的心理谜团》这本书中那些装病者,如内莉会习惯性地通过自残来获取医护人员的关怀,实则是在将身体化为“呐喊的媒介”,试图以生理疼痛换取曾经一度缺失的被共情体验。这种代偿机制,恰如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中的“垂直分裂”(vertical split)机制:患者们真实的心灵自我被深深压抑,取而代之的是以症状为载体的虚假自体来示人。装病者如同困在玻璃罩中的蝴蝶,他们每一次振翅(症状)都试图引起外界的关注,却始终因罩壁(谎言)的存在而永远无法触及真实的温暖。
孤独的囚徒与自由的恐惧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指出,焦虑源于“自由的眩晕”。故事案例中的装病者厄尼深陷分离焦虑之中而千方百计地虚构自己的疾病,实则是将弥漫性的存在性孤独转化为一场场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威胁”——比起直面被遗弃的深渊,发烧或疼痛提供了更可控的避难所。这种策略与海德格尔(Heidegger)的“沉沦”概念不谋而合:通过沉溺于“常人”(das Man)的疾病叙事,个体得以逃避本真性的重负。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位故事主人公梅丽莎沉迷于让她自己成为病例讨论的焦点,实则是将存在主义的“被看见”需求异化为医学凝视的对象。此刻,她的身体俨然成为一座剧场,观众是医生,剧本是症状,而谢幕的掌声则是她对抗存在性虚无的微弱胜利。
从童年到成人:谎言的进化与存在的延续
童年撒谎的幽灵
弗洛伊德曾言:“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童年期的谎言常是创造力的体现,但当成长环境充斥“不可用的客体”(如冷漠或控制的父母),谎言便从游戏退化为生存工具。装病者往往在早年经历中饱受情感忽视,成年后的症状伪装,实则是儿童期策略的病理化延续——正如精神分析师科胡特所言:“真正的创伤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无人回应的绝境。”
编织命运的丝线
加缪(Camus)在他的那本《西西弗斯神话》中写道:“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对装病者而言,问题或许是:“如何在不自杀的前提下,继续存在?”他们的谎言如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动作,虽充满荒诞却蕴含抵抗。书中那些装病患者们每一次装病,都是对命运之石的短暂驯服;每一次被揭穿,则是巨石滚落的惊心时刻。但在这无间循环中,他们至少确认了自己仍在“推石”的途中。
获得治愈的希望
重建镜映与联结
精神分析师科胡特一度强调,治疗的核心是提供给病患“矫正性的自体客体体验”。对于装病者,医生或治疗师需超越症状的表象,倾听谎言背后那些声嘶力竭的呼救。例如,案例主人公内莉需要的其实并非医学诊断,而是有人能够真诚地对她说一句:“你的这些痛苦本身已值得被看见。”倘若被种共情性回应稳定、持久地包裹,便能够逐渐修复其破碎的自体,将他们那“疾病剧场”转化为真实的情感联结。
拥抱自由,书写本真
萨特强调:“人是自己行动的总和。”治愈装病者,医护人员及病患家属需要引导其从“自欺”走向“本真选择”之路。例如,帮助梅丽莎意识到,她其实无需通过疾病来让成为环境的焦点,而是可以主动创造价值——正如卡尔.荣格所言:“终其一生,我们都是为了要成为自己!”这要求个体直面自由的重量,在责任的承担中重塑存在之意义。
在谎言的裂缝中照见人性之光
《我有病,我装的:解开装病背后的心理谜团》这本书中装病者那一幕幕令人匪夷所思、荒诞离奇的故事,宛如一面面扭曲却诚实的镜子,映照出人类心灵的普遍困境:我们极度渴望被理解,却恐惧被看穿;内心追求掌控,却沦为症状的囚徒。但在这充满悖论的旅程中,亦隐藏着救赎的可能——正如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灵魂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所写:“倘若你信任自然,信任那些艰难,信任那些孤独……你的生命将从此生长,如河流般宽广。”或许,当装病者放下疾病的假面,他们终将发现,真实的自我远比谎言中的角色来地更加丰盈、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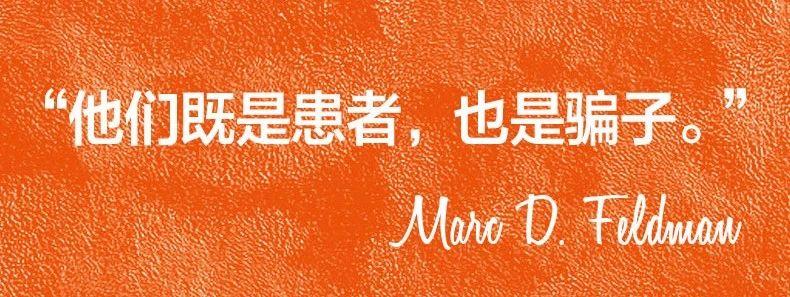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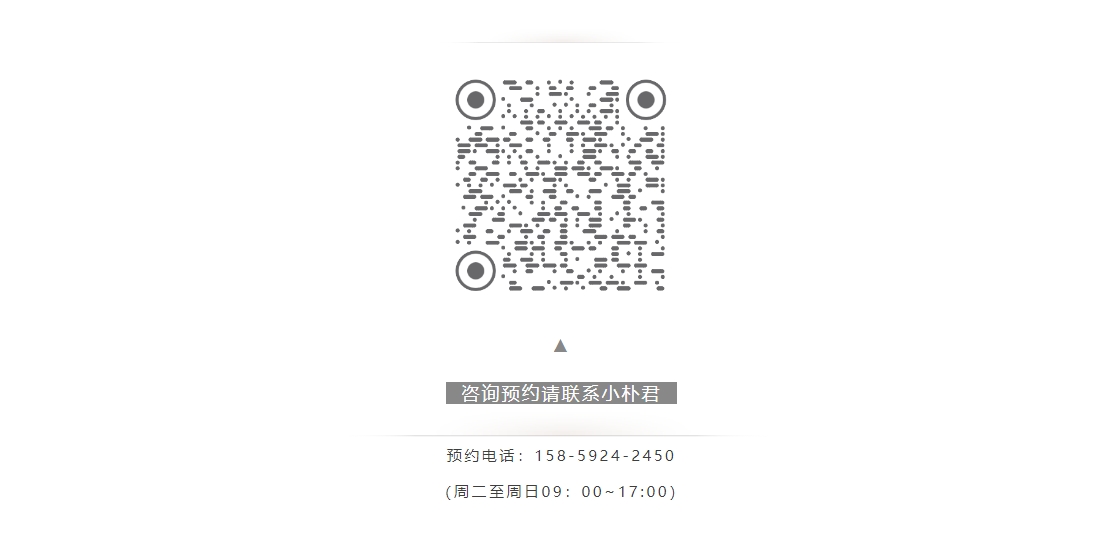
参考资料与推荐阅读:
LEMMA, A. (2005), The many faces of ly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6: 737-753.
[美] 马克. D. 费尔德曼.我有病,我装的:解开装病背后的心理谜团.盛文哲,林颖(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5.01.
[美] 彼得·A. 莱塞姆.自体心理学导论.王静华(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年: 2017.1.
[美] 海因茨·科胡特.精神分析治愈之道. 訾非(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3.
[法] 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9.1
[丹] 克尔凯郭尔.畏惧与颤栗 恐惧的概念 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3.5.
[法] 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闫正坤,赖丽薇(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