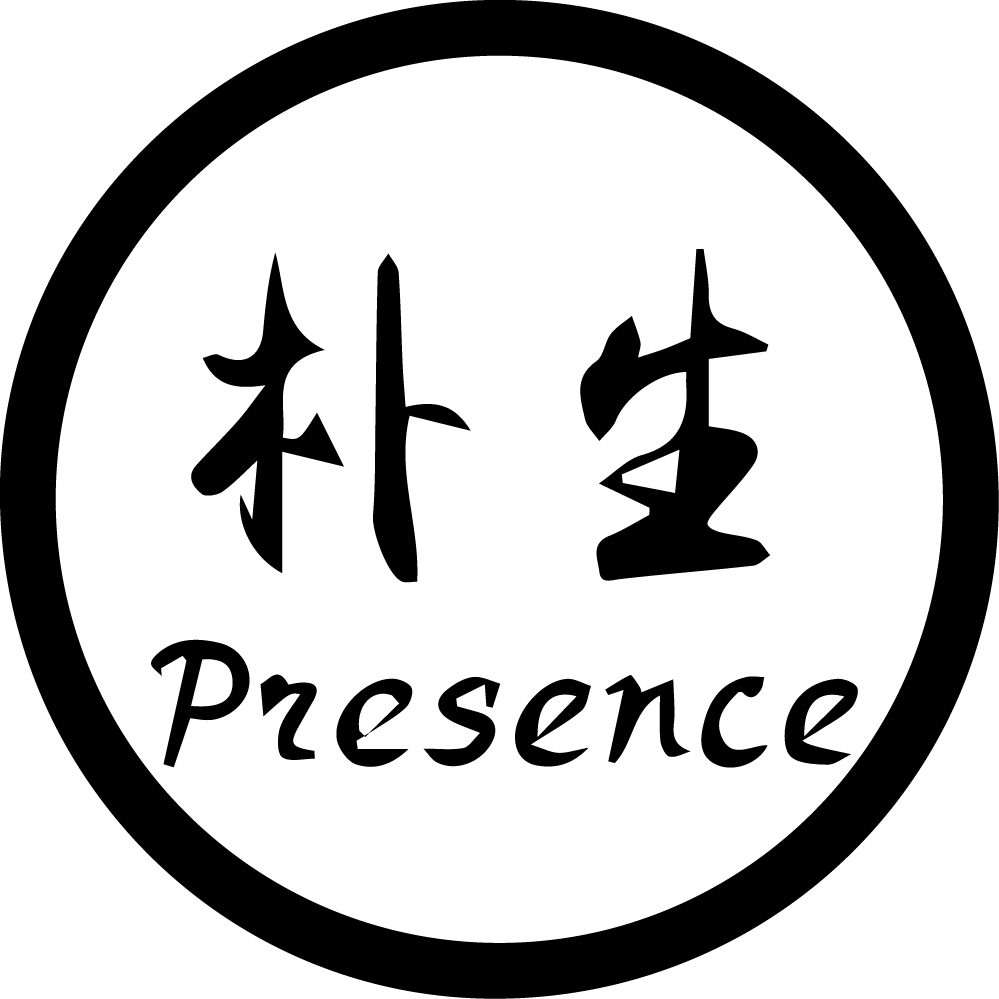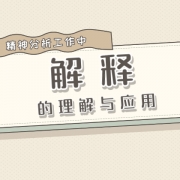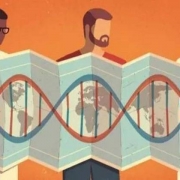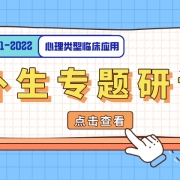论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1937)
原文:Sigmund Freud
编译:厦门朴生心理
我们从众多临床实践经验中得知,精神分析治疗——即使得个人从自己的神经官能症症状、压制和性格的扭曲中的得以解脱——是一项十分耗费时间的工作。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需努力缩短分析的疗程。此种努力毋庸置疑:因为它们要求以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与最有利的权衡考虑作为根据。然而,早期的医学科学认为神经官能症没有什么治疗的必要,认为它是由一些隐秘的创伤所导致的,所以在这些努力之中,可能也仍旧有一些急躁的轻视的迹象在起作祟。如果到现在,神经官能症的治疗已然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它至少应该被尽快地处理。
在此方面,奥托·兰克做出了一些特别积极的努力,这在他的著作《出生的创伤》(The Trauma of Birth (1924))可以看到。他认为,神经官能症的真正的来源是婴儿出生的过程,因为这个出生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一个孩子的对自己母亲的原始依恋(primal fixation)没有得以顺利的修通,而是作为一种原始压抑被留存下来。兰克希望,如果这个原始创伤可以通过日后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来得以处理,那么整个的神经官能症症状将会被治愈。
因此,这一小部分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将会省去其他的那些不必要的分析历程。然后,几个月的时间应该足够去完成这小部分的分析工作。毫无疑问,兰克的论证颇具胆色和创新;但是它没有经受住批评性检验的考验。而且,它的这个理论是在(一)战后生灵涂炭的欧洲和美国的繁荣兴盛的美国之间形成强烈对比之下才构想出来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儿童的一个缩影,它是期待将精神分析治疗的节奏来适应飞速发展的美国社会生活。
我们尚未见到到在兰克想法引导下有大量奏效的临床个案。这可能就像是我们打电话叫火警,让消防官兵来扑灭一个由于一盏倒掉的油灯点燃的房子,却仅仅只是让他们从熊熊大火中找出那个油灯一样。毫无疑问,这样的方式将会大大限制消防官兵的作用。兰克的试验的理论和临床治疗实践现在都已经过时了的事情了—如同美国的繁荣一样。
甚至在战争以前,我自己也曾经采用过一种短、快精神分析治疗的方法。在那段时间,我曾经接收到一个年轻的俄国人的个案,那是一个被金钱宠坏的公子哥。他在一个私人医生和随从的陪同下,以一种完全无法自立的状态,来到维也纳找我接受分析。 经过几年的分析工作,本来是可以重新让他变得独立自主起来,也可以唤醒他对生活的兴趣和调整她重要的人际关系。但是,治疗进展戛然而止了。在治疗成为后来的疾病的基础的童年的神经官能症中,我们没能做得更多,并且,很明显,病人发现他现在的状态非常的舒服,没有意愿去迈出任何前进的脚步,而这些前进的脚步将会带领他进一步接近治疗的结束。这是一个治疗本身让自己停步不前的案例:正是这个案例取得的部分疗效(神经官能症状得以缓解)将自己置于面临失败的危险境地。
在这个困境中,我采取了一个异常胆大的措施——为分析设定一个时间限制。在开始一年的分析工作之初,我告知病人,接下来的这一年将是他的接受分析疗的最后的一年,不管他在最后留下给他的时间里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起初,他还没当回事。不过后来,他马上就确信我是非常认真的,然后就开始渴望获得改变。他的阻抗减弱了,并且在他接受治疗的最后那几个月,他能够使所有的记忆在脑海中重现并且发现其中所有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对于理解他的早期的神经官能症和控制他的现在的疾病似乎是十分重要的。当他在1914年的盛夏时节离开我,结束治疗的时候,没有一点怀疑,就如同我们一起取得如此快速的进展的那段时间,我相信,他获得的治愈是彻底的、永久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5年,没有什么证据能反驳这个结论的真实;但是我们有必要把一些信息保存下来。这个病人后来一直留在了维也纳,尽管他并未取得太大的社会成就,但是他得以在社会中立足。
但是,在这期间,他的良好的健康状况有几次受到过疾病的侵扰,而这个疾病只能被解释为他多年来的神经官能症的衍生物。多亏我的学生Dr. Ruth Mack Brunswick的努力,一个短期的治疗过程使得一切都得以回归正轨。我希望,Dr. Ruth Mack Brunswick以后会对这些情况作简短的报告。
在这些侵扰中,其中一些仍旧与移情的剩下部分相关;并且在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尽管这些移情成分存在的时间短暂,它们仍旧呈现出了明显偏执的特点。
然而,在其他的侵扰中,然而,致病的内容属于病人的童年经历的碎片,而当我在跟谈做分析时候,这些内容还没有显现出来,而是现在冒出来。这就像手术之后的缝合线或者坏死骨头的小碎片一般,是不可避免的。我发现,这位病人的痊愈的过程几乎和他的疾病史一样令人感兴趣。
后来,参考了其他的分析师的经验,我也在另外的一些个案中采用了这种限定时间期限的治疗方式,关于这个恐吓的策略的价值有且仅有一个结论:倘若我们恰好撞到对治疗合适的时间,它就会有效。但它不能确保完整地完成这个任务。 相反,我们可能确定,一部分内容在威胁的压力之下将能够获得;但同时,另一部分内容可能会被阻止,并因此而被埋藏,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治疗的努力就是失败的。
这一次,分析师已经限定了疗程时间,他不能再扩展期限,否则病人会对他失去所有的信任。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是病人再与另一个分析师继续治疗,虽然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改变面临着需要耗费一段新的时间来开始和对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的抛弃。关于通过强制策略来限定适当的时间期间,也没有一个通用的规则;这个决定必须由分析师的经验来确定。因为一个错误的预估是无法弥补的。“老虎只跳出一次”,这句谚语非常适合这里。
关如何来加快一个分析进程的技术问题的讨论把我们引到了另一个更让人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否会有一个东西作为一个分析自然结束?是否有可能,所有的分析工作都能有这样一个结束?根据分析师的普遍说法,似乎是这样的: 当病人还在为一些普通人身上所熟知的那些缺憾而深深抱怨时,或者他们对此极力辩解时,我们就会经常听分析师们说,“他的分析还没有完结”或者“他还尚未接受完成的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分析的结束”这个模糊词语的含义是什么。从临床实践的观点看,它是很容易回答的。当分析师和病人他们不再因分析而见面时,一个分析就结束了。
当大概满足以下这两个条件足时,分析的结束才会发生:首先,是病人应该不再遭受他的症状的痛苦,而且是也应该已经克服了他的焦虑和压抑;其次,是分析师应该判断,如此多的、被压抑的材料被意识到,如此多的费解的材料被解释了,并且如此多的内部的阻抗被克服了,病人就没有必要害怕一个与致病的过程有关的重复。
如果我们被外部的困难阻止而没能达到这个目标,最好把它称作一个不完整的分析,而不是一个未完成的分析。
分析的“结束”同样意味着是需要更大的雄心壮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要追问的是,是否分析师已对病人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假如我们继续他的分析,不再期待在他的身上会有进一步的改变发生。就好像,通过分析可以达到绝对的心理正常水平–一种水平,而且,是一种我们能够感觉自信的水平,能够保持稳定,如同,我们可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病人的每一个压抑,并成功地填补了他记忆中的所有的缺口。我们可能首先查阅我们的经验,以了解是否这样的东西确实发生了,然后借助我们的理论来发现它们是否有一些发生的可能性。
每一个分析师都会有一些治疗效果令人满意的个案。他成功地疗愈了病人的神经官能症困扰,并且,这些困扰没有再复发,也没有其他类似的症状。没有对这些成功的决定因素的洞察,我们也不会取得成功。
病人的自我并没有明显地改变,而他的困扰的病因本质上是创伤。毕竟,每一个神经官能症的病因都是混合的创伤。两个本能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过分强烈,这都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自我对改良的反抗—或者早期不成熟的自我所不能控制的创伤的影响。
这样说来,就有两个因素的混合,一个是根本的因素,另一个是一个偶然因素。根本的因素越强,创伤就越容易导致一个固着和留下一种发展的困扰;遭遇的创伤事件越严重,即使本能的情况是正常,它的有害的影响当然也就越明显。
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造成创伤的病因为分析提供了更为有利的领域。只有当个案遭受到来自创伤因素的主要影响时,他才有可能在无比艰难的分析中成功。由于病人的自我功能已经提高,也只有病人成功后,他才会用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像他在自己早期生活中做出的那些不适当的决定。
只有在这样的一些个案中,我们才能说一个分析已经确切地结束了。其中,分析已经做了所有它应该做的,已然无工作可继续了。确实,如果以这种方式恢复了健康的病人不会再产生另一个需要分析的疾病,我们不知道他的免疫力有多少是由于我们为他除去了太严酷的考验的仁慈命运。
在被扰乱和受到限制的程度来自本能的原始力量与自我的不利的转变需要它们进行防御性斗争—这些因素对分析的效果是不利的,它可能使它的分析无法终止。
我们也认为,这个首要的因素——本能的力量,也是第二个因素——自我的改变,出现的原因;但是,后者似乎有它自己的一个病因。而且,我们确实必须承认,至今,我们对这些事情的了解是不足的。
只有现在,他们才成为分析研究的主题。在这个领域,分析师的兴趣,在我看来,似乎是被完全错误地引导了。不要去探究疗愈是如何通过分析来实现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阐述,真正的问题应该是:阻碍这样治愈的障碍是什么?
因此我希望通过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它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直接起源于分析实践的问题。一位男子,他自己曾经在接受分析过程中取得很大的效果,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对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对作为他的竞争者的男人和对他所爱的女人,并没有摆脱神经官能症的阻碍;并且通过他认为比他优越的其他人,他让自己成为分析的主题。
他自己对自我的批评性结论得到了一个十分成功的结果。他和他所爱的女人结了婚,并变成了被他当做对手的朋友和老师。他和他的前任分析师也保持这一种界限分明的关系,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但在后来,麻烦出现了。没有任何确定的外部诱因,这个曾经接受过分析的男子开始对他的分析师变地敌对起来,他责怪分析师没能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分析。他说,分析师本应该已经知道并且应该已经考虑这个事实:一段移情关系不可能是完全积极、正面的;他早就应该注意到可能会出现负性移情。
分析师为自己辩解说,在分析的那段时间里没有出现负性移情的迹象。但是,即使他没有能够察觉到负性移情的一些模糊的迹象——鉴于那段分析工作中,分析的有限的视野,这是无法完全排除的——它仍旧是可疑的,他认为,仅仅把这种负性移情的可能存在指出,是否能够使病人身上当前一个处于沉寂状态的主题(或者,按我们的说法,一个“情结”)激活。
事实上,为了激活它,在分析师的部分,确实需要做出一些不太友好的行为。此外,他补充说,在分析期间和分析之后,不是每一个分析师和他的个案之间的好的关系都被当做是移情关系;也会有一些友好的关系,它们言语现实并被证实是可行的。
接下来是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中出现了相同的问题。一个老大不小未婚女子,由于腿部的几处疼痛而无法正常走路,而且是从青春期开始就这样了。她的情况明显是带有一种癔病的特点,并且她曾经拒绝过很多种治疗。一个持续了三个季度的分析治愈了这个问题,并且还帮助病人发展成为一个杰出的和可敬的人,也使她找回了正常的生活。
在她康复之后的几年种,她总是遭遇到一些不幸。她的家庭中遭遇了一些灾难和经济上的损失,并且,随着她渐渐变老,她看着爱情和婚姻之中的所有幸福的期望一点点消失。然而,这位曾经的病人,勇敢地面对困难,她在困难时期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我记不太清了,是在分析结束的12年后,还是14年后,由于大量出血,她不得不接受一项妇科的检查。 检查中发现了一个肿瘤被,她不得已,接受了子宫全部切除的手术。从这个手术的时候开始,这个女人再次病了。她爱上了她的外科医生,沉湎于对内部的可怕改变的、受虐狂式的幻想中——隐藏着她的浪漫的幻想——表现得使分析中的进一步努力下也难以实现。
直到她的生命结束,她都没有回归正常。这个“成功的”分析治疗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们不需要对它抱有太大的希望;它是我初为分析师时的个案。毫无疑问,这位病人第二次患病可能与她的第一次已经被成功地克服的疾病有着相同的根源:它是那些相同的、被压抑的冲动的不同的表现,这些被压抑的冲动没有通过分析得以完全修通。但是,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有后来新的创伤事件,就不会有症状的再次爆发。
我所举的这两个例子,是从大量的相似的例子中特意地挑选出来的,足够用来开展一个我们正在考虑的主题的讨论。怀疑的、乐观的或者是有雄心的人对它们有不一样的看法。第的人会说,现在,证据表明,甚至接受成功的分析治疗也不能让一个曾经被治愈的病人免除受到后来其他神经官能症的侵扰,另外一种神经官能症是与最初的神经官能症来自于相同的本能根源——即旧病复发。
其他人可能认为,上述的结论不可靠。他们会反对说,这两个例子分别追溯到二十年和三十年以前的分析早期;并且,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然取得了更深的洞识和更广知识,而且我们的技术也随着我们的新发现而变更。他们会说,如今,我们可以要求也可以期待一个分析所带来的疗愈应该是持久的;或者,如果一个病人再次患病,至少他的新疾病不应该是他以前的本能的困扰以新的形式的重现。他们将会宣称,我们的经验实际上并没有迫使我们限制这些可以改进我们的治疗方法的要求。
我选择这两个例子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们是很久之前的个案。显然,越是近期的成功分析案例,我们所能加以讨论的实用性就越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个案痊愈以后的发展将会怎样。乐观者的预期清晰地推测了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并非不须证实的。
首先,他们总结,确实存在一个永久的并有待解决的本能冲突(或者,更正确地说,一个自我和本能的冲突)的可能性;其次,当我们治疗他的一个本能冲突时,可以说,我们可以给他注射预防任何其他的这样的冲突的预防针;我们有能力,为了预防的目的,去激起一个这种类型的致病冲突,因为在那段时间这种冲突还没有任何征兆会暴露出来,而且,这么做是明智的。我抛出这些问题,并没有打算现在就立刻解答它们。也许,在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对它们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
通过理论的思考,它们可能会被部分得以阐明。但是另一点业已明晰:如果我们希望对分析性治疗履行这些更为严格的要求,我们的分析之路将不能把我们带向或通往一个分析时间缩短的领域。
(本文内容为厦门朴生心理原创,版权归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所有。
转载请联系15859242450,并注明出处。)
预约咨询请添加助理微信

编辑: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