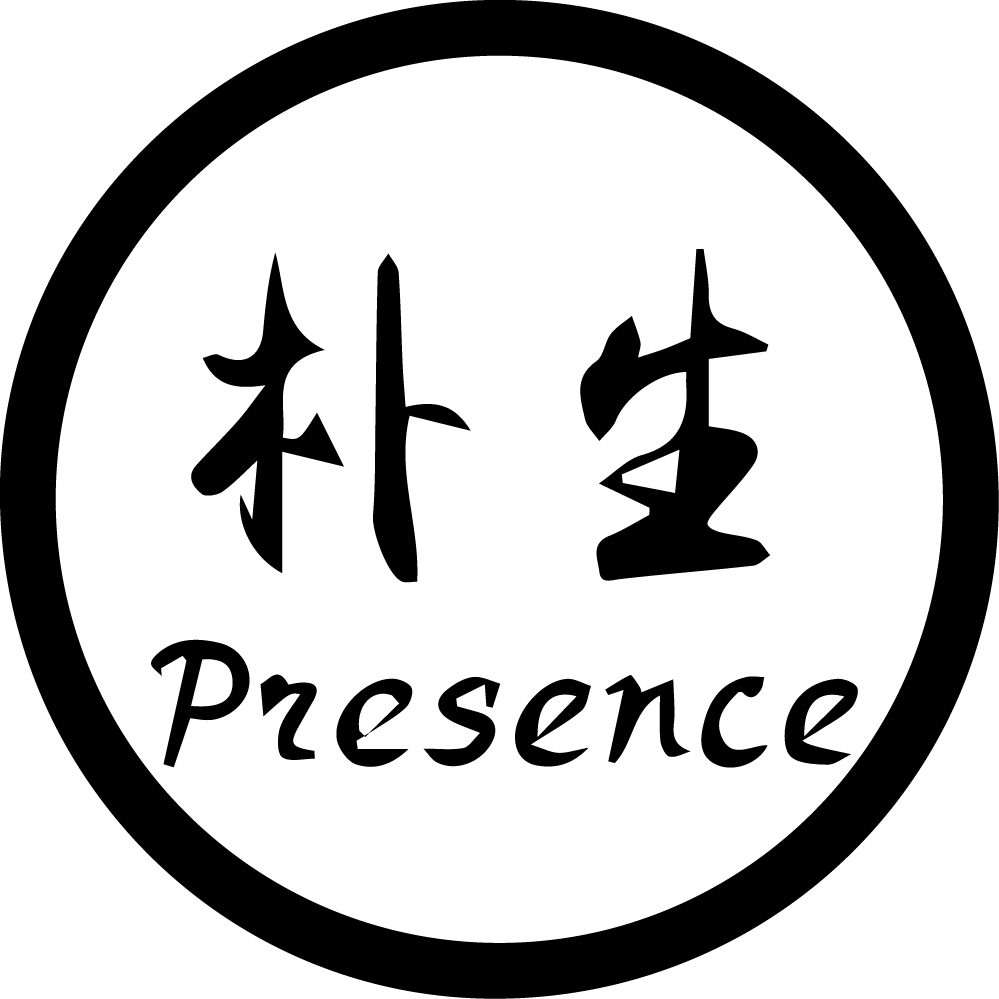心理健康,不是一味的去适应社会
原文: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编译: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 盛文哲
排版设计:Youngsen
在弗洛姆看来,真正的心理健康绝不是一味地“适应环境”或“没有痛苦”,而是一个人保有清晰的感知力、真实的情感能力以及面对现实的勇气。在访谈最后,主持人问他:“我们是否还能在这样的世界中保持健全的理智呢?”弗洛姆认为:“可以的。但你必须愿意忍受孤独,愿意拒绝大多数,愿意与那些清醒者一同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联结。
虽然这段访谈拍摄于半个多世纪以前,可当今的社会环境跟那时有着诸多的形似之处:地区硝烟不断,各大经济体之间充斥敌意、排斥与攻击,人们对于未来感到情景渺茫,大部分人内心困顿不安。因此,这段六十多年前的采访对话,在今天的我们听起来仍感振聋发聩,富有警示与启迪意义。在10.10世界精神卫生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一同重温这段对话。基于种种可说、不可说的原因,本文在原始访谈内容上有所删减。
心理健康议题与我们当代这个社会
事实上,我想说明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或许一个人可以呈现出一些问题或症状并意识到自己有些不太健康,这是这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内心可以几乎体验不到任何的主观幸福感,却对此麻木无感、毫无觉察。因为这样的人只能自欺欺人,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我深信,许多所谓“心理健康“的正常人,客观来说,比一些自认为有心理问题的人要病的严重的多。因为这些敢于承认自己有病的人,至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和症状。
怎么可能一个人生病了却对此完全没有感觉?甚至没有任何症状?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人都病了。就像 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创作的小说《盲人国》(The Country of the Blind)中所描写的那样,人们把大家所共同表现出的状态命名为“正常”。具体来讲,我们当今的文化提供了各式各样可供人逃避的渠道。所以,如果让一个人单独呆上三天三夜,没有网络、手机、电视、以及各种媒体和其他任何的娱乐方式,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人都会因此而精神崩溃掉。而如今的社会文化,以“大众娱乐”、“消费”等名义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逃避现实的手段。如此一来使得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可以说,他们从更深层次上忘记了自己是人的存在。
心理健康,究竟是指的什么?
我个人所理解的心理健康,可能跟很多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理解的心理健康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觉得,心理健康就意味着是对环境的适应。也就是说,你没有比一般的人更“病态”,也就是要被局限于社会可接受的不幸福的平均水平,不要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这是一方面。如今,也有很多人将心理健康定义为没有生病(the absence of sickness),而何为生病呢?这往往被人们理解为无法适应社会,或者适应不良,或者是表现出某些具体的症状,比如失眠、焦虑、具有幻觉、酗酒等待。而我,并不会从“没有生病”这个角度来狭隘地理解人的心理健康议题,而是从更为积极的视角——幸福感(well-being)的层面来进行理解。
幸福感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东西,它很难给出清晰明确的界定;可当一旦你体验到,既会对它有深刻的感受。不过,幸福感这东西不一定经常会遇到。因为那些真正呈现出幸福状态的人,在今天这个环境下是极为稀少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幸福感的人,他们身上会流露出真实的活力和生命力。这跟那种强迫性的精力过度旺盛不同,而是一个人内在自然生命力的展现;另外,这些人不会畏惧独处,而且他们在跟别人共处时不会有想要逃避的冲动;另外,我们可以这些人身上看到,他们会表达自己真实的喜悦之感,他们可以在恰如其分的情景下适度体验到悲伤;他们对别人具有浓厚的兴趣、对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和感知、有意愿建立广泛的联结、可以做出恰当的回应,对这世间万物也可以做出恰到好处的回应。
如果我们把心理健康理解为主观上的感受,那它究竟包含哪些元素?
我相信,跟其他一些感受类似,很多人对自己心理健康的理解大多也是幻觉。现如今,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状态特被得好,因为他们服用了镇静剂、苯乙胺、酒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他们必须要通过不断追求娱乐,或者是以某种执念的方式来做事。很多人对于自身幸福感或心理健康的表达,实际上或许并不可信。我觉得,心理健康的人群,他们拥有敏锐、深刻、强有力的意识觉察,而且能够恰如其分地对这个世界给予回应。也就是,既不偏执古怪,同时又具有旺盛的精力与生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心理健康可以理解为一种感受现实的能力,对自我及世界的现实感知力:如其所是地体验,并能够做出恰当的回应。
当今的社会上有哪些因素在侵蚀我们的心理健康?
首先,就如我刚刚所说的,有很多诱惑或者途径在侵蚀我们的现实感。另外,我们当今社会中的大部分价值导向都聚焦于对物质的生产和消费,��受到这种“物欲横流”价值取向的影响,我们要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也不断诱导大家要去消费。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将自己“异化”了;我们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尽管我们口口声声说着要鼓励发展个性;我们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我们自以为是在依照自己的意愿、想法、信念来做事,而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被社会或者商业环境操纵着,从而失去了个人的目标;我们愈发地跟自己疏离开来,几乎体验不到任何的情绪感受,我们也不愿有深切的情绪体验,而是只想让自己可以与众不同;我们被大众所裹挟,极度恐惧偏离社会的步伐,哪怕只是轻微的一点点的偏差。尽管如此,很多人还在自欺欺人的否认现实。
提升社会大众对心理健康的关注,这项举措会带来帮助吗?
我真诚的希望,这会给我们带来帮助。但我也有所担心和顾虑。我相信,确实有很多人提供这方面的帮助,也确实想要有所改善。同时我也担心,如今社会大众对心理健康议题的关注也面临着一些风险,这就像发展至今的精神病学、精神分析理论或者心理学一样。我十分担心,有些心理学已经变成了单纯地帮助人们更好的去适应社会,仅仅是让人们更好的发挥功能而已。或者说,今天的很多心理学方法或者心理健康干预,正面临着沦为“体系说教者”的危险。也就是,它们一味的帮助人们去适应一个体系,要人们被迫大量地从事生产和消费,去与社会大众盲目地融为一体,而人们自己对此却毫无觉察。而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所经受的苦难,恰恰也是内在的乏味和无意义感的来源,这就会带来危险,令他们真正的生病。人们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或问题,而他们也会因此寻求帮助。这是,就会有一些心理学工作者跳出来,说你不应该有所不满,如果感到不满,就说明你有心理问题。于是,就有人会来“治疗”你、“矫正”你,说教着让你要全盘接受,要接受这般无意义的人生。而最终,他们会给你一场“体面的葬礼”。
我们一般只会说一个人“疯癫”了,您觉得可以将这个词用来形容社会环境吗?
如果,我们用“疯癫”(insane)这个词来表达缺乏真实、健全的理智(sanity),那我确实认为这个社会都可以陷入疯癫之中,而且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社会或时代都陷入过疯癫。我也担心我们现在正走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除非我们有做出根本性的改善。另外,我还想补充的是,对于健全的理智,存在两种理解:整个社会可以看似非常的理智健全,因为人们都适应了它以及其中的规范;但与此同时,从人类个体的健康和福祉来看,这样的社会也可能是疯癫的,对于每一位活生生的个体而言,所有那些伟大的规训或者是规范,都是关于人的存在和人类的整体,它们往往都基于个人核心理念,即服务于人类和人的价值,将对人的价值优先于具体的社会之上,无论这是怎样的社会以及怎样的价值体系。
我所理解的健全的理智,是一种理想的心智状态。它融合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批判性的立场、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实现精神自由和完整人格的关键。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
具备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这是“理智感”的基石。它要求个体能够不盲从权威、传统或大众意见,而是敢于对一切社会和现象保持怀疑、批判和“不服从”的能力。这是一种主动运用理性功能的心智状态。
反对盲从,心智健全的思考方式,其核心在于反对人云亦云的“陋识”。弗洛姆认为,真正的理智是可以清醒地、独立地做出判断,而非被动地接受外界灌输的观念。
人道主义价值观,这种理智并非纯粹的工具理性,它必须服从于“人性和人道社会的目标”。换句话说,独立思考的方向应该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尊严和福祉服务。
对社会的批判:在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中,人的理智能力常被异化,导致心理不健康。因此,健全的“理智”也隐含着对社会病态的批判和对一个“健全社会”的向往。
生活在如今这个时代下,一个人还能保持健全的理智吗?
当然可以了。我相信,只要一个人真正的努力去尝试:首先要认识到现实中确实存在诸多失望,还要勇于面对环境中某种程度的孤独感。因为这些,都是生活在一个缺乏健全理智的时代中让自己依然能保持足够理智的必然代价。其次,如果一个人能够想方设法与这种孤独感共处。我们可以通过跟他人建立深切、真实的联结,跟那些曾经活在世上之伟大的人产生内在的共鸣,跟那些曾经让自己保持健全理性之人进行深度的沟通,比如曾经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思想家。甚至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有这样依然有意愿保持健全理智和清醒的人存在,但不多。关键在于,我们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具有敢于说出真相的能力,去认同人类中的那一部分:那就是要有足够的现实感,同时又不让自己陷入绝望之中。
您对未来社会和人类发展有怎样的期待?
我相信,我们已经发展除了一定程度的健全理智,也具备了足够的知识和洞察力。只要我们能够克服对于物质生产和消费的狭隘执着,便可以构建一种更具有真切、自在满足感的文化环境。
原作者介绍: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著名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是上世界二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他于1934年赴美,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机构讲学,并先后执教于墨西哥国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等高校,于1980年病逝于瑞士洛迦诺。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的人文主义思想有机融合起来,关注现代人在自由、孤独与异化中的心理困境,强调真正的心理健康在于保持健全的理智、爱与自我实现,而非盲目适应社会。他以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文笔,创作了大量学术著作和普及性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爱的艺术》、《存在的艺术》、《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精神分析的危机》等。
(本文内容为厦门朴生心理原创,版权归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所有。转载请联系15859242450,并注明出处。)
预约咨询请添加助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