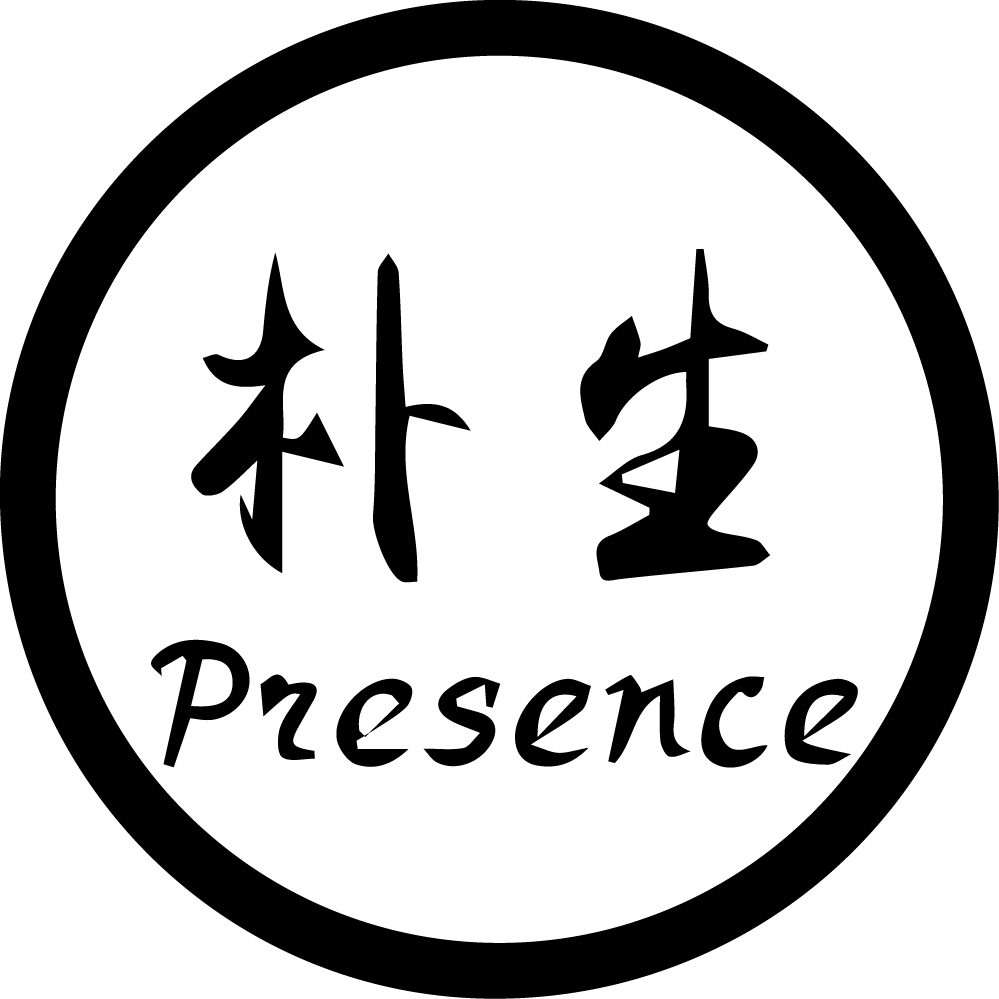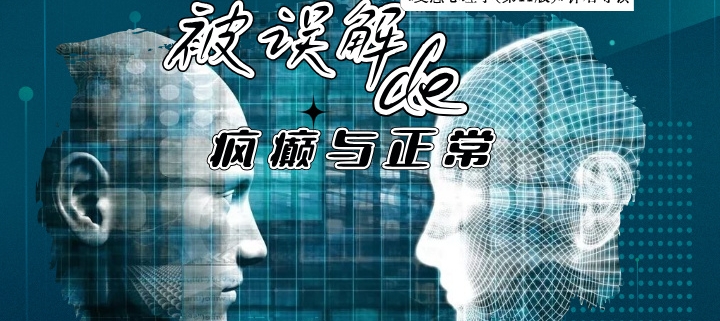《变态心理学》译者导读Ⅱ:我们真的比“疯子”更清醒吗?
这个问题听起来像个荒诞的笑话,但它却直击了精神疾病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来定义“疯狂”?与大多数疾病不同,精神疾病往往无法通过血液检测、X光片或手术刀找到明确的病变。皮肤病变和身体外伤可以通过肉眼观察,肿瘤可以通过医学仪器检测并切除,但精神疾病呢?它通常表现为认知、情感、意识和行为的异常,而这些异常在身体上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这不禁让人想起英国精神病学家莱恩(R.D. Laing)的那声发人深省的疾呼:“那些宁死不与社会抗争的人,被我们视为正常;敢于承认自己丧失了灵魂的勇士,却被我们看成是疯子。” 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能够通过脑成像技术发现某些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基础(比如阿尔茨海默症),但对于大多数精神疾病,我们依然缺乏明确的生物学证据。那么,医生如何判断一个人是“疯子”?正常人装疯卖傻是否无法被识破?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医学,更关乎我们对“正常”与“异常”的理解。
当正常人被贴上“疯子”标签 罗森汉恩实验 1973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大卫·罗森汉恩(David Rosenhan)做了一项轰动全球的实验。他招募了8名志愿者(包括他自己),让他们假装听到幻听(比如“滴答声”或“砰的一声”),然后去精神病院就诊。除了这个虚构的症状,这些“假病人”表现得完全正常。结果令人震惊:所有8名假病人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或躁郁症,并被强制住院。即使他们在入院后表现得完全正常,医生依然认为他们是为了出院而“假装正常”。甚至,他们的正常行为也被解读为病态——比如,写日记被记录为“强迫性书写行为”,与其他患者交谈被解读为“偏执性社交活动”。更讽刺的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反而察觉到了这些假病人的异常,认为他们是在“演戏”。罗森汉恩的实验揭示了精神病诊断的一个荒诞真相:一旦被贴上“疯子”的标签,你的所有行为都会被重新解释为病态。
所谓的精神疾病究竟是生物学异常还是社会共识?或者说,疯癫的历史是不是一部权力的历史,而非单纯的医学史呢?在中世纪,疯癫被视为一种神圣或神秘的状态,与宗教和超自然力量相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疯癫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学和戏剧性意义。欧洲发展到古典时代,疯癫被禁闭和隔离,成为一种社会秩序的威胁。而在现代社会,疯癫又有着被医学化的浓重色彩,成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比如,同性恋在1973年之前一直被列为精神疾病,直到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它才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删除。类似地,在某些文化中,“附身(possessed)”、“灵魂出窍”等现象被视为灵性或宗教体验,而在西方医学中则被归类为精神障碍。这种社会性定义的本质,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对“正常”的集体想象;另一方面,它可能将少数群体的行为病理化。例如,19世纪的“歇斯底里症”曾被用来描述女性个体的情绪异常波动,实则是当时父权社会对女性自主权的一种无情压制。
那精神病学如何一度成为政治工具的呢?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禁闭疯癫者并非出于医疗目的,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理性统治。禁闭是一种权力机制,通过将疯癫者排除在社会之外,强化了理性对非理性的统治。在冷战时期的苏联,精神病学被用作政治镇压的工具。异见者常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或“偏执型人格障碍”,并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院当中。这种“被精神病”的现象,揭示了诊断背后的权力游戏。正如福柯指出的,“精神病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它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 前苏联的案例警示我们,精神病诊断可能沦为权力的附庸。当科学与政治纠缠时,医学的客观性很可能将荡然无存。
对疯癫或者是精神类疾病的理解与治疗有一段漫长的黑历史:在患者脑袋上钻个洞来“驱赶”邪祟;把病人关进笼子里浸入冰水直到几乎将他们溺死,好把他们从疾病中“吓”出来,就像在治打嗝一样;把病人绑在一张转椅上飞速转动;将患者放在一个木制圆筒状的大蒸笼里死命地蒸煮,以此来让疯子恢复理智;摘除患者身体部位如牙齿、扁桃体、结肠和宫颈,而这些据信都是会感染疯癫的病灶;韦病人注射氰化物、疟疾或巨量胰岛素以引发其昏迷;甚至会将一件类似冰锥的锐器插入眼眶把脑子搅成糊糊。而在当时,以上每一种疗法都曾被奉为拯救患者的神奇妙方。
曾经,精神疾病一度被人们当作是恶魔附体或是体液失衡所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精神疾病被认为是由超自然力量引起的。古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精神错乱是由于灵魂附体、巫术或恶魔作祟。治疗方式通常是驱魔仪式,旨在释放病人大脑中的“恶魔”。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体液学说,认为精神疾病是由于体内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失衡所致。这一理论虽然现在看来不科学,但在当时是一种理性思维的进步。
到了中世纪,精神病院曾经有一段黑暗的历史,其中充斥着不可告人的囚禁与折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拥有绝对权威,精神疾病被视为“恶灵附体”。精神病患者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像牲畜一样用锁链拴住,供人参观。伦敦的伯利恒皇家医院(Bedlam)是最著名的精神病院之一,患者遭受的折磨远比疾病本身更为痛苦。这一时期的精神病治疗方式主要是囚禁和隔离,而非真正的治疗。
随着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理性角度重新审视精神疾病。伏尔泰和卢梭等哲学家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大脑疾病的病态分泌物。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进一步提出,很多宗教信仰其实是心理投射的结果,旨在满足神经元的需求。这一时期,精神病学逐渐从宗教中分离出来,进入医学领域。
20世纪初,精神病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迎来了前额叶切除手术与药物革命。1935年,葡萄牙医生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发明了前额叶切除手术,认为通过破坏大脑前额叶可以治愈精神疾病。这一手术在短期内使患者变得温顺,但长期后果极为严重,许多患者失去了人格和自主能力。肯尼迪总统的姐姐罗斯玛丽·肯尼迪就因这一手术导致智力严重下降,生活不能自理。随着化学知识的进步,20世纪中叶出现了精神药物革命。1950年代,氯丙嗪(Chlorpromazine)这款药物的发明标志着精神疾病药物治疗的开端。1970年代,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如氟西汀(Prozac)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抑郁症的治疗。然而,精神药物的滥用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许多患者因过度用药而产生依赖。
当代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已不再局限于弗洛伊德的“性驱力”理论,而是融合了英国客体关系理论(如梅兰妮·克莱因)、依恋理论、自体心理学(如海因茨·科胡特)、北美关系学派、主体间心理学视角等众多分支。精神分析师克莱因提出,婴儿早期的“偏执-分裂心位”和“抑郁心位”是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例如,一个无法整合爱与恨的婴儿,可能在成年后表现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特征。这些理论强调,精神疾病不仅是症状的集合,更是内在冲突与关系模式的映射。比如,抑郁症患者可能潜意识中将愤怒转向自身,而焦虑症患者可能被未解决的分离恐惧所困扰。依恋理论(约翰·鲍尔比)揭示了早期亲子关系对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压力下能有效调节情绪,而矛盾型或回避型依恋者更容易陷入抑郁或焦虑。例如,一个童年被忽视的人,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反复验证“我不值得被爱”的信念,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会通过探索这些“隐形剧本”,帮助患者理解潜意识中的重复模式,从而打破恶性循环。
此外,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也给予一个个在疯癫边缘痛苦挣扎的个体重新直面生命的虚无与自由的勇气。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这种自由带来的不仅是可能性,更是沉重的责任。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关注四大终极议题:死亡、自由、孤独与无意义。例如,焦虑症患者可能因恐惧死亡而过度控制生活,抑郁症患者可能因意义感缺失而陷入虚无。治疗师不会提供标准答案,而是陪伴患者直面这些议题,在不确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意义。正如哲学家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所说:“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当代心理治疗实践中,存在主义与精神动力学常常被交织使用,试图帮助痛苦的灵魂寻找生命的“锚点”。例如,一个因童年创伤而自我否定的患者,既需要探索潜意识的冲突(精神动力学),也需要重新定义创伤的意义(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可能会问:“如果这段经历是你生命故事的一部分,你希望它如何影响未来的章节?”这种整合疗法如同在潜意识的迷宫中点亮一盏灯,同时为患者提供直面存在的勇气。
未来的精神病学需要超越单一的生物学视角,采用整体化的方法来理解精神疾病。这意味着不仅要关注基因和神经递质,还要考虑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仅是大脑功能的改变,更是对极端环境的社会性反应。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许多患者因害怕被贴上“疯子”标签而不敢寻求帮助。未来的精神病学需要推动社会包容,减少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和偏见,鼓励更多人主动关注心理健康。例如,冰岛这个国家已经通过社区支持计划,将精神疾病患者的再住院率降低了40%。此外,每个人的精神疾病表现和病因都不尽相同,因此未来的治疗应更加个性化。通过基因检测、脑成像技术和心理评估,医生可以为每位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例如,针对抑郁症患者,基因检测可以预测其对特定抗抑郁药的反应,避免无效治疗。未来的精神病学应更加注重早期干预,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压力管理和社区支持,减少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例如,芬兰的“心理健康急救”项目,通过培训普通人识别心理危机信号,显著降低了自杀率。
精神疾病的漫长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对“疯狂”的理解不断演变,疯癫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病理现象,它是随着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变化而不断被重新定义的,而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定义和治疗方式。尽管医学不断进步,或许我们仍未完全理解“疯狂”的本质。未来的精神病学需要在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点上寻找答案,以更好地帮助那些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们。精神病学的未来不仅是科学的进步,它更呼唤真切的人文关怀。我们需要在医学技术和社会包容之间找到平衡,确保每位患者都能得到尊重和有效的治疗。正如福柯所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或许,正是那些被视为“疯狂”的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性的独特视角。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精神疾病的定义和干预将面临更多挑战。我们也需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来尝试尊重并理解每个人的独特性,避免将“不同”简单地等同于“异常”或“障碍”。毕竟,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说:“在个体中,疯狂是罕见的;但在群体、政党、民族以及时代中,疯狂是司空见惯的”。
-
Nietzsche, F. (1887). Madness is rare in individuals but common in groups, parties, nations, and epochs (as cited in Beyond Good and Evil , 1886). -
Foucault, M. (2025).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Jung, C. G. (2023). 人类与象征 . 周党伟, 林颖,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
Laing, R. D. (2022). 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 . 林和生,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所 -
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Camus, A. (2020). 西西弗神话 . 李玉民, 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