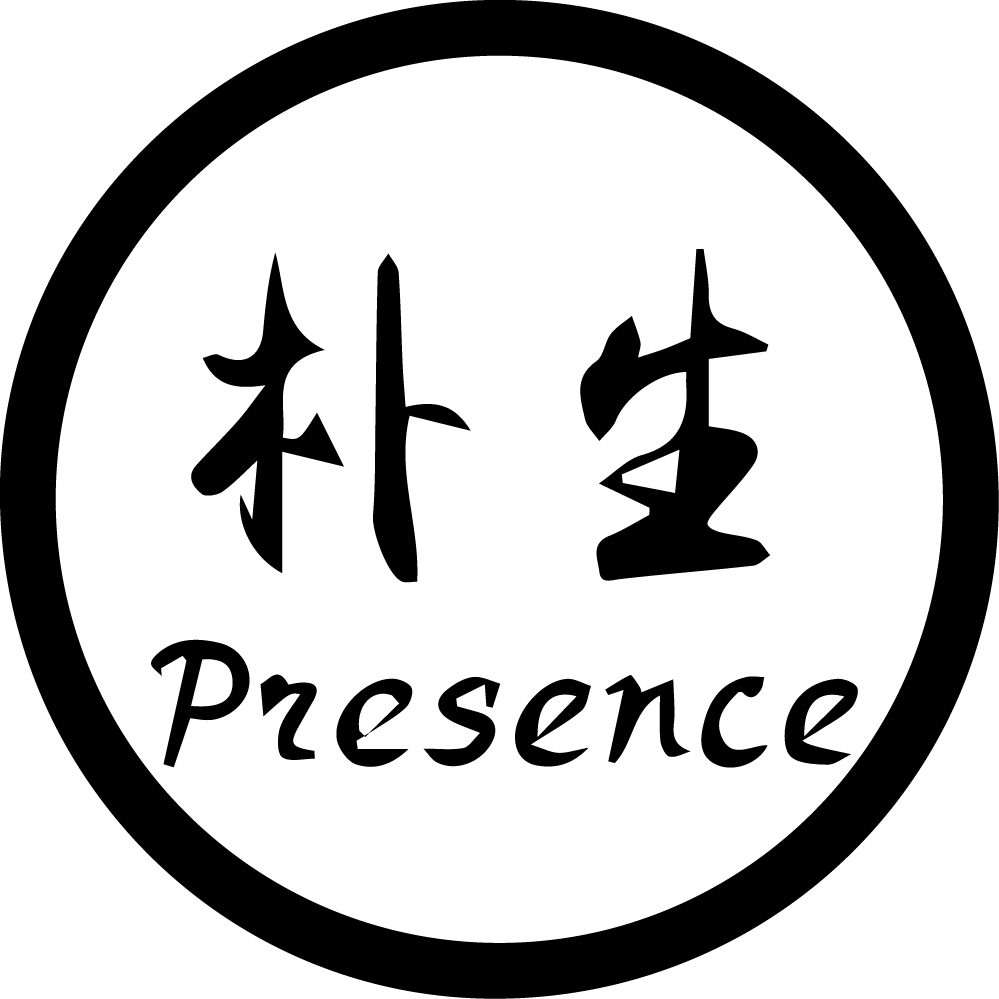精神分析主体间视角的4个基本临床态度
精神动力学主体间视角咨询工作的4个基本临床态度
原创: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
精神动力学主体间视角下的临床咨询工作,具有鲜明的人性化态度和温暖的理解视角:
我们在咨询中所面对的来访者,他们每一位都是完整的、鲜活的个体;心理咨询师需要通过共情的方式来促进理解而不是仅仅是同情;咨询师要努力跟来访者共同叙事,赋予他们新的意义;咨询师还要避免心理病理化的标签。
主体间视角下的临床心理咨询工作:面对着完整的个体
人们会带着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寻求我们的帮助,通常他们都有的一点是和同事、朋友、伴侣之间,让他们感觉不满意的人际关系,一些更具体的问题以症状的形式体现出来,比如 DSM-5或ICD-11临床诊断系统里标明的一些症状。很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专业领域有时候会把人看成各种失去功能问题模块的组合,这些成问题的模块功能都可以分别加以咨询,不同的部分可能都可以转介到针对这个部分做工作的特定领域的咨询师、专门工作者。比如一个常常生气的人,他会被转介到愤怒管理的咨询师做咨询;一个在性方面有问题的人可能送到性咨询师做性心理咨询;那些有恐惧症(如恐高或社交恐怖) 被送去接受暴露咨询;当我们追求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时,我们可能会转向药剂师开药,很快地调解。但是在精神动力学主体间视角的临床咨询工作方式里,我们把人看成完整的存在,而不是失去功能的模块组装在一起的东西。不管这个人的问题/症状是什么,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人向我们呈现出来,他对这些烦恼的理解,同时,这些烦恼、问题对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问自己,来访者是怎么形成他的这些问题的?什么样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让他有这样的问题?
临床咨询案例:文森特
我的同事伊丽莎白博士和我一起记录并撰写了文森特的个案报告。文森特有强迫性性成瘾的行为,他花费很多很多时间去浏览网上色情作品,找性工作者,而且会重复看他收藏的性作品。我们可以把他看成一个性成瘾的人,所以把他送去接受成瘾咨询或者去性成瘾同伴支持小组,但我们不这样做,我们需要管理好我们自己的焦虑并且去探索他是怎么形成这些问题?
文森特成长在一个军事家庭,这个家庭中所有的成员都在军队服役,他把自己称为从军队出来的顽童,用这样的话掩藏他作为父母都是军人家庭经历中的辛酸和痛苦。在他3岁时,他的父母离婚了,他被送到双亲在海外服役的军事基地里,一次可能在一个家长那住几个月,文森特说他的爸爸是一个超级有男子气概的人。他的爸爸和他爸爸身边的军人同僚营造出过于男性化、男权、男子气概的氛围,对女性有不太好的轻蔑态度,这些都是文森特在他爸爸那的成长环境。一个例子可能是这些大人他们会吹嘘自己又睡了多少女人,征服多少女人,而且其中他们吹嘘有些征服的女人甚至是未成年少女。文森特的童年和青春期时代是这样成长起来,文森特对人性的追求、追寻被他的爸爸批评为不男人,需要摒弃,不好的行为,在他的爸爸面前他感觉十分羞耻,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一个男人。他还记得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喜欢一个女孩,想要写诗去追求这个女孩,女孩拒绝了他,这让史蒂夫得出一个结论自:己在这女孩面前还不够男人,不够阳刚。然后当他成为一个年轻男性时,他感觉很难接近、靠近女人,他怕靠近女人后这些女士都会发现他不够阳刚,没有男人气概,不值得这些女士注意青睐。他想要追求女士,但他对自己的认识:认为自己既没有男子气概,又十分无能,所以这些让他性生活,对爱情的追寻变得十分破碎,无法做到。这样的过程导致文森特把强迫性浏览色情电影,找性工作者当成自己的安慰剂,来应对压垮他的无能、没有男子气概的感觉。
在文森特进入咨询后,他的咨询师是伊丽莎白博士 (一位非常有吸引 力的年轻女咨询师) 通过咨询师的同调,表达理解和关怀,文森特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在伊丽莎白面前他感觉自己没有受到羞辱,这个 状态和他在他的父亲和他父亲的军人同僚面前很不一样,通过和詹 妮弗的互动接触,他意识到是他曾经的生活体验,所处的生活环境 让他产生了自己不男人,自己很无能的感受,所以他关怀、关爱自己的方式,调节自己情绪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工作到了面临结束时,因为伊丽莎白要结束在这个机构的实习,那个时候文森特仍然会浏览在线色情视频,但他已经不再找性工作者,他开始尝试去和他同龄身边的女士接触,而且发现有些女人还对他有好感,所以把文森特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而不是把他看成由分别不同、仅仅是可以得到调整的功能模块部分所构成。这涉及到帮助文森特梳理他的发展成长历史,而且帮助他理解这些经历对他形成中的男子气质,男性感受产生的负面、消极的影响,他找到一份工作并且能在工作中感觉到自豪、骄傲而不是感到羞耻。
主体间视角下的临床心理咨询工作:共情而不是同情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心理咨询师常常会混淆共情和同情的区别。来访者说他的宠物狗死了,我们那时候可能会这么表达说自己可以理解他的丧失,因为我也曾经有这种经历,我家的宠物狗之前也死了。这样的分享是基于同情的分享,因为他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使用了自我暴露技术,它在有些时候可能是无害,哪怕它无害,可是它仍然会把话题带偏,从对来访者的内在探索,对意义的追寻中偏离到别的方向上去。因为我们的协议是我们有两个人,但我们两个人共同同意去探索一个人的心灵意义,所以主体间取向的临床心理咨询工作是两个人共同努力来为一个人形成新的意义,两个人是咨询师和来访者,其中的一个人指的是来访者。而咨询过程中咨询师的一些非必要的自我暴露所具有风险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需要带到咨询中,替换了以来访者为中心的状态性质,这会让来访 者产生一种感觉:他们首先需要关心我们的状态、我们的需要,而把咨询完全用来关心他们自己、探索他们自己是有问题/会带来羞耻感。
我们在咨询当中,面对的是一位活生生的人,而过于机械、过于僵化/冷淡的态度也一定会阻碍对来访者进行同调式的理解,所以咨询师能在给予温暖和提供理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且不要走捷径 (捷径是通过自我暴露的方式,给来访者提供一些同情)。
主体间视角下的临床心理咨询工作:与来访者共同叙事
心理同调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来访者一样的经历才能理解来访者在经历这些后的感受,如果我们把来访者所有的焦虑、恐惧、抑郁的体验都亲身体验一遍,我们很快会在工作中耗竭,去体验别人有什么感觉,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一个的确能带来推动新的经验组织的方式是:这个人感觉到他自己的情感、感觉被其他人理解了。
通过我们共同形成成长发展的故事,让我们能清楚知道,这个来访者为什么有当前的感受和行为,这会给我们带来理解。比如不是所有人都上过战场,但是在咨询里,如果一个军人是来访者, 我们和他共同理解上战场,在战场中的经历对这个特定的军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见证过很可怕的死亡/破坏的人,这些见证到的死亡和破坏肯定是非常可怕、糟糕,我们也许忽略掉在这些过程里,他的恐惧背后可能也有非常兴奋、刺激的部分。我们可以猜测军人的感受是什么,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和军人在一起,共同拼凑,找出他的感受以及这些感受的所蕴含意义。
这种悲悯之心在面对心理创伤时,两个人可以共同面对,对双方有很大作用。但悲悯和同情一样,仍然和我们强调的共情性的同调是有一定的差别(不一样) 。比如咨询师说:“我也可能会非常害怕。”这个回应其实并一定会带来伤害,但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咨询师说:“我在想,这会不会是一种特别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痛苦体验。”这便是一个提供同调式理解的尝试。随着咨询的深入和开展,这种基于同调的观察反馈能帮助来访者更好地有情感整合和情绪的调节,而且我们也需要接受自己有可能不准确,并接受来访者对我们的更正。因为军人也有可能会说:“我当时没感觉害怕,我觉得特别有活力、有生命力。”有心理学家也发现,单纯的生理疼痛并不是一个会带来病理的问题,创伤也不是那个特定事件本身,创伤是因为在这个情境里这个人的体验是超载的 (当事人自身无法承受) ,而且也缺乏一个有同调、有共情能力的人能理解他的体验,这才带来了创伤,所以不是所有军人都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心理咨询师的任务是去理解这个特定的军人为什么罹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因为什么原因没有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童年的成长经历和他在军队中的同伴帮助他有更多的韧性,可以去应对战场中的恐惧还是导致他变得更脆弱?最重要的一点是共情不仅仅是一种倾听的姿态,去帮我们理解对方的体验,共情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允许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也参与卷入其中,这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自体客体体验,让情绪得到整合,拥有更好的调节能力,去理解个体的意义,并在主体间的领域里能参与其中,为另一个人的成长和转变提供巨大的便利和贡献。
这不等于我们要详细去分享自己的个人成长经历,自己个性的细节,我们应该有的认识是我们需要知道——如果不是透过我们自己的视角、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是无法理解对方的感受、体验、经历。一方面我们需要时常考虑到我们作为咨询师自己的体验、经历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来访者的反应、反馈,我们对来访者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我们没有这样的责任/任务去塑造或引导对方的心灵,帮助他们形成目标。我们的任务是共同构建、共同理解来访者是怎么形成他当前生活存在的形式,在这样一个探索旅程中,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俩是伙伴一样的的合作关系。
主体间视角下的临床心理咨询工作:祛疾病标签化
人们常常在感觉到一些失败时,会使用一些疾病名称或标签来病理化自己或责备、批评自己,特别是当他们自我责备的倾向是作为一个非常幼小时就建立起来的组织原则时,人们更会这么做。这常常来自他们的主要养育者或者是对他们有重要意义的人,这些周围的人在他们很小时可能会病理化他们。所以当我们识别出一 些问题时,能以一种更有适应性和发展性的视角去看待这些问题而不像来访者一样单纯地病理化、用疾病来给他们自己贴标签,这对于更好的理解心理问题和一些症状,促进心灵的成长和疗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来访者责备自己懒/固执/有自我挫败的行为,那些心理上的烦恼可能也会被心理病理化,变成诊断手册中的诊断或医生口中的一些精神或心理问题专业词汇;人们可能也会多少了解一些心理诊断和疾病标签,他们也会给自己贴上这些标签。但是给人贴上人格障碍/精神心理问题的病理化标签,而这些标签都打在挣扎着,在他们当前的逆境、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的有痛苦的人身上。当一个人用病理化的方式描述他们自己的心理困境时,我们总能听到他们父母的声音,能感觉到好像也是他们的父母在给他们贴标签。这个可能会被贴上有心理病理问题标签的人,在我看来,我会把他们称为“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抗争和努力的人” ,所以他们是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尝试做到最好,哪怕他们的一些行为可能不具适应性,但仍然让他们感觉到一定程度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体统合感。他们可能在一个非常压迫、失控的童年环境里挣扎着,试图维持住最基本的自体感受和自我价值感。如果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我们遇到的来访者,这可以帮我们有更多思路去探索来访者的一些防御和问题行为。
在传统的意义上,防御的功能是阻隔在我们潜意识里感觉不被接受,我们不想了解的一些感觉和愿望。在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经典框架中,防御是为了潜意识不让意识知道一些东西。但在当代精神分析主体间视角中,防御的功能和目的是为了维持自体的统合感,它保护我们不被我们自己或他人感觉到不好的情感、想法所伤害。我们把一些感受包藏裹藏起来,因为我们害怕这些感受会破坏我们 和我们所需要的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些感受暴露出来,这可能会在我们自己心里激发起羞耻的感觉。
参考资料与拓展内容:
Peter Buirski/Pamela Haglund.(2001).Making Sense Together:The Intersubjective Approachto Psychotherapy.Jason Aronson Inc.Publishers.
皮特·博斯克/帕梅拉·哈特兰德(美国).主体间性心理治疗[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