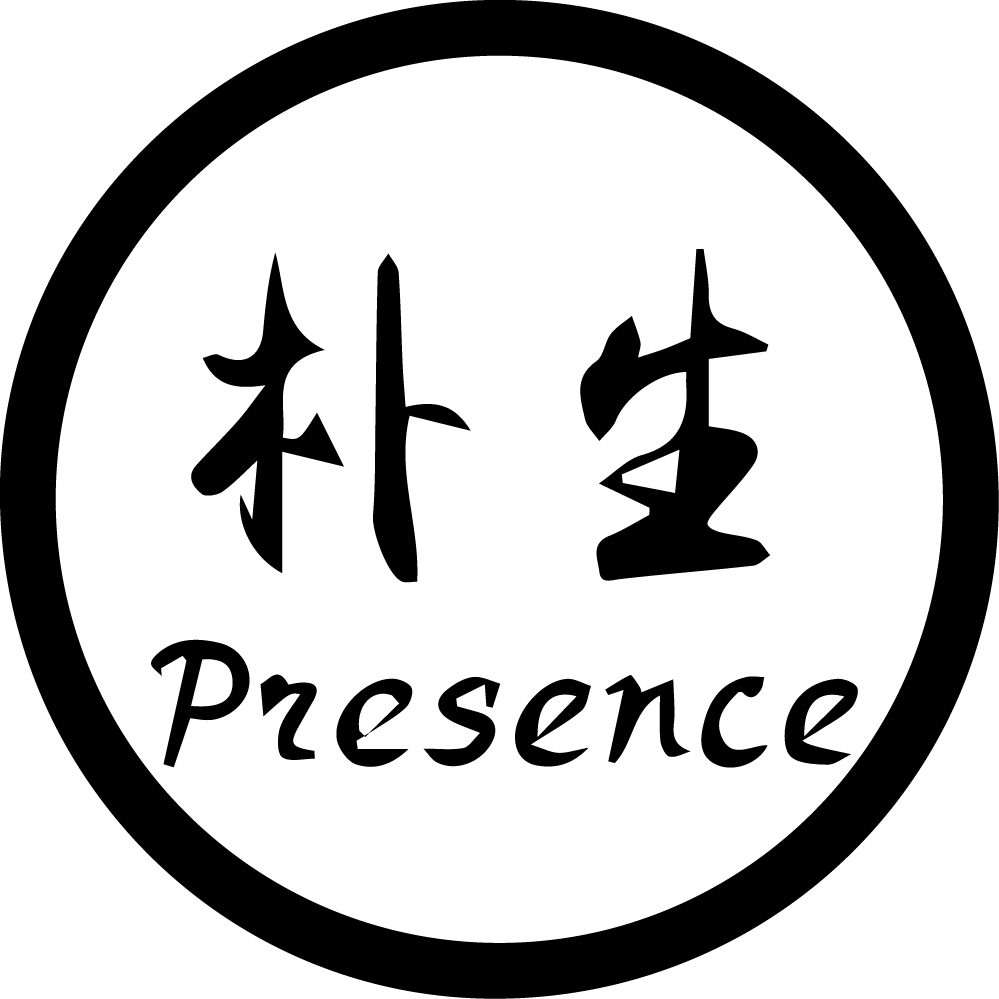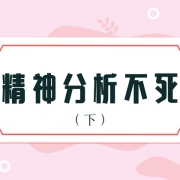工作/治疗联盟与对联盟的突破

(Alliances and Misalliances)
原文:Jerome S. Blackman, M.D.
编译: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
01.关于工作联盟
工作联盟是临床心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是针对如何跟那些太快地离开治疗,不成熟地结束治疗,或者在治疗中有很多阻抗的来访者进行工作。这个概念实际上有不同的命名方式,它本身也有不同的构成的部分,今天我们先从其中的一个概念——工作联盟入手。与此相关的,还有检验治疗联盟和治疗框架这两个概念。我们也会涉及到在治疗工作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些会使我们进入到治疗中的不当行为。
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有不同的联盟。比如婚姻联盟,在这种婚姻联盟中,我们跟我们结婚的对象会有一些誓言,我们互相会有一些期待。还有一些其他联盟,比如我们称之为亲子联盟。这个联盟意味着在孩子逐步长大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他们期待在你这获得一些什么,你也学会在孩子身上也期待得到一些什么。当我们讲到夫妻联盟,和我们后面提到的这个亲子联盟的时候,很显然,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联盟,比如你所工作的公司或者你所工作的大学,在这些不同的联盟之中,你们相互之间都会有一些期待。
当我们谈到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咨询)的时候,这个工作本身是试图帮助来访者去理解他们头脑中还尚未理解的那些内容。为了使得这项工作进行,我们也需要达成一些协议或者一些合约。
最初开始试图去概念化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的这种特定的合约,特定为这一内容给予一个定义的人,就是Ralph Greenson这个位精神分析师。在这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访者能够很清晰地识别出我自己有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会有一些情绪性的问题。而且来访者会清晰地理解你将要帮我来明白我的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到底是从何而来。
我们现在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实际上这没有那么简单。之所以说它没有那么简单,是因为这一观念的背后,它取决于病人的一些主要的基本功能。这些功能中的第一个就是能够进行自我观察的功能。当我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大多数精神病性的来访者。
因为你可能会从一个精神病性的来访者那里听到这样的内容:我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在监视我,他们想要杀死我。你进一步问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吗?他们就接着说,意思就是别人想要杀死我。他们可以去识别出那些让他们饱受痛苦的问题,但是他们无法识别出自己内在的心理问题。
同样的事例也适用于那些非常抑郁的、但并不愿意去接受任何可能对他们有治疗帮助的来访者身上。这些来访者开始跟你工作的时候,你问他说,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觉得是什么触发了或者引发了这个问题呢?来访者可能会这么回应你,我这种状况已经持续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不是非常确定它到底是因何而开始的,但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原因。因为大多数时间,我感觉还不错,但只是在偶尔的一部分时间,我感觉很糟糕。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征。这个时候,你可以进一步地跟他探讨Peter Fonagy提出的关于”心智化”的这个概念。
如果来访者是这样跟你说的,他说,”没什么原因,我觉得我大脑好像有点什么问题”。这样的来访者可能更加适合于抗抑郁剂的药物治疗,他们并不适合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因为他们并没有一个动机要去理解自己内在的无意识的那些原因。现在还有一些病人无法识别出他们自己的这些问题。
右这样一女病人。她是24岁的年轻女性,她本来是在非洲工作,后来她就逃离了那个地方。原因是什么?她经历了一次惊恐发作。当时,她整个人躺在了地上,浑身发抖,持续了几分钟的时间。
在她的问题出现两天之后,她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跟她说,让我们来谈谈你的问题吧。她跟我说,谈什么?然后我跟他讲,史密斯小姐,应该是医疗机构相关的一个人员给我打过电话,说你在非洲的时候有过一次惊恐发作。她说,哎呀,那个呀,那不是啥问题,我今天没事儿。
然后接下来我们花了30分钟的时间讨论她近期的这些生活。我们发现,原来她在非洲工作的时候和当地的一位男性约会,但是最终这个男性转而投向了其他女人的怀抱。好像我们的来访者用了很强烈的压抑这种机制,试图忘记这位男士跟她分手然后去找别的女人,给她带来的这些感受。
在整个治疗的这个45分钟里,我们去讨论了她生活的一些细节。随着这些讨论,她开始逐步能够意识到她自身的这个惊恐发作,跟她之前这个关系的结束是有一些关系的。具体是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可能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这里存在着某种联系。虽然暂时还不是非常清晰。她也在这一节结束的时候,想接下来继续回到治疗中,跟我继续去讨论、去找到这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前面描述的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我和她进行这种工作联盟的一个基础性的部分。
最近我有一个50来岁左右的男士来访者。他老婆抓到他在外面乱搞女人。在评估环节,我就直接问他,你见我只是为了让你老婆高兴、取悦她吗?然后他就开始大笑,他说,要是我自己,我才不来见你呢。但是我真的还不太想离婚。我说,这就意味着你并不承认你有什么情绪上的问题,你的问题只是在于你不想失去你的妻子。然后他说,我还是觉得我可能有点什么问题吧,因为我其实自己都搞不清我为什么出轨,我还是挺爱我妻子的。我接着说,我确实同意你,我觉得你可能确实有点问题。我觉得这一点你说得没有错,但我只是不太确定你到底有哪些问题导致了你现在的这种行为。然后他想一想说,医生,我可能知道一点点。然后他开始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所以通常在治疗的开始,我也许并不会直接去问来访者他们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而是问他们对于自己问题的思考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第一原则。我们和来访者都要同意说他自己确实有某些问题,而且你们对于他的问题是什么也要有一致性的这种同意和观点。对于这种问题的判断是你们接下来进一步工作的基础和聚焦的那个点。那在工作中,我们会做一些什么?我们会试着去理解你们所定义的问题的背后的无意识方面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他当下生活的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讲的是工作联盟的第一原则,就是识别出来访者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工作联盟的第二原则,就是来访者必须同意并愿意去讨论他们的问题,而且你们也只能讨论这些问题,你也做不了什么其他别的。
刚才我们讲合约,其实有两端。一端就是来访者愿意去讨论他们的问题。合约的这一端,你也要做出一些承诺。你要做的是你愿意跟来访者去讨论他们的问题,以及你愿意帮助来访者去理清他告诉你的那些问题背后的、那些他们可能还尚未意识到的原因。如果来访者想让你抱他们,这是不被允许的。还是基于这一原则,唯一允许的只能是交谈、谈论。
最近我有一个来访者,在电话中跟我说,医生,关于我的问题,我写了15页,我要不要发给你?我就说,不用,等你来到我诊室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当面去讨论吧。当然,即便我说我们只能去讨论,我也让他相信我对他描述的这些问题是感兴趣的。但对他而言,可能最有帮助的方式就是我听他讲。我也想听听他来说他是怎么理解他的这些问题的,我也尽可能地帮他去加深他的这些理解。
大家现在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我现在讨论的治疗其实是限于心理动力学治疗。它的对象是成年个体。当我们的来访群体开始变成青少年甚至是儿童的时候,整个情境开始变得更加得复杂。在这个工作联盟中,也需要包含进他们的父母。
我们下面看第三条原则。来访者需要对你所说的话进行一些回应。来访者开始讲述他们的问题时,你会帮助他们进行一些理解和一些这种建构概念化的这个过程,但来访者接下来需要对你所说的进行反应。因为我们作为治疗师的理解,并不是完全准确的,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到底有哪些是真正了解的,还有哪些是不清楚的。
我有一个来访者,他咨询的时候就拿了一个小笔记本,老是想把我说的话都给记下来。我就跟他说,你这样让我感觉我像一个老师一样,你得把我说的话都记下来,因为我可能要给你一个考试,你一定要把那个考试通过了。我跟他讲,这不是我们工作的方式。但是你跟我互动的这个方式本身,你难道不觉得挺有意思的吗?让我们想一想你到底在做什么。
当我们开始用工作联盟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不可避免的,来访者一定会做很多他承诺不做的一些事情,或者不做一些他承诺做的事情。这时候就是一个契机,我们可以去澄清那些内容,进一步地去进行理解。
还是回到刚才记笔记的那个来访者身上。当我邀请他开始注意到他对待我的方式就像对待一个老师一样,然后他开始记得说,可能之前上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老师打过他。我们接下来就进一步去讨论了他的那个记忆,并且去讨论了那些事情到底是如何对他施加影响的。
我们再接下来看一看这个工作联盟、这个合约的其他一些部分。还有来访者需要同意他们会准时到达以及准时离开。这当然会给双方都带来一些压力。治疗师有的时候自己可能也会迟到,也不一定会按时。对来访者而言,有的时候可能治疗时间到了,但他们正在说着什么非常重要的内容。
如果我或者我的来访者迟到一两分钟,我通常不太觉得这里边有什么意义。我之前有一个男来访者,有一次迟到了3分钟。进来的时候就说,抱歉,抱歉,Blackman医生,很抱歉,我迟到了。我看了一眼表说,就几分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迟到了3分钟,你知道吗,这代表了我朝向你这个父亲角色的攻击性的情感部分。但有些时候,来访者要么是到的特别早,要么是迟到了,或者到时间不走,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我们都可能会找到某种意义。
那我们讲到工作联盟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来访者需要付费。而且他们不是只付费而已,他们必须按你所要求的去付费。因为你是专业人士,他们付费一定是基于你的个人意愿和个人要求。
当然在美国,心理治疗可能有一些付费的惯例,跟中国不太一样。我通常会在一节治疗结束之后向来访者收费。但我知道在中国,有的时候大家可以提前收十次费用。当来访者不付费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他打破了你们之间的这种合约。通常,这意味着来访者对你保有某种愤怒的情绪。来访者为什么对你生气呢?这背后当然有意义了。一般这种现象相关于,这类来访者通常感觉到在自己父母那缺乏爱意、得不到足够的爱。
但是为了理解这些,你们两个人之间必须先要有一个合约、有一个协议。他必须得按你要求去付费。这样的话,他后面去打破这个协定的时候,才会给你一个机会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每一个治疗师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则,就是关于来访者如果缺席一次的话,他是否需要付费。不同的治疗师到底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也有巨大的不同。但不管别人怎么样,只要你决定了你自己的这个付费规则,比如说如果来访者缺席的话,他是否需要付费,如果付的话,要付多少,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合约、有这样一个付费规则在,而且来访者提前知道并且同意,那这就达成了一个付费规则。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点稍微有些复杂的情况。就是来访者来了,你跟他说,你的问题是什么?他立马就开始跟你讲述他的童年经历。当然,我们知道童年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他们所讲的一定是非常有用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如果你就让他这么讲下去,他可能就一直跟你绕弯子,不会直接告诉你到底是什么让他在35岁的时候决定给你打电话。
所以,如果来访者如果在初始访谈中一开始就讲这种原生家庭问题,当他讲了几分钟之后,你一定要打断他。首先,向他表现出你对于他的问题是感兴趣的,以及让他注意到好像到现在为止,你还不知道他当下生活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来访者没有清晰的主诉,或者否认他自己有什么主诉,或者他上来跟你报告早期原生家庭的这些问题,这些都意味着来访者正在使用防御机制。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让他先停下来,帮助他去表达他现在当下生活的那些问题,这些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
如果来访者一开始并不能准确地识别出自己的问题,他可能跟你工作几次之后说,我感觉好多了,再见了。我有一个有进食障碍的来访者,他几乎每三四次治疗都要跟我说,我觉得最近好多了,咱们什么时候结束呀?你觉得我可以结束了吗?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不是很确定,你现在还吐吗?还暴食吗?他说,嗯,这些情况还存在。
02.关于治疗框架
那我们看看第二个要讨论的理论家Robert Langs。关于Robert Langs,其实我们要讨论的是设置。设置就是治疗的一个框架。Langs指出,在治疗室之外,和治疗师之间的任何交流都是对于这个框架的一个打破,或者是一个中断。这一些都是具有意义的。当然,从现实逻辑上来讲,有的时候你确实要和来访者有一些治疗室之外的对话,比如说,来访者给你打电话跟你预约,这个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还有一些情况是来访者治疗结束之后跟你发信息、给你打电话,或者时间到了不走,就一直想跟你呆在一起。
比如说,来访者直接把你放在等候室里的,只是借阅、不可以带走的杂志拿走了,这也是对框架的一种中断或者是打破。因为基于Robert Langs的这个理论,他已经在框架之外还想再从你这拿一点什么东西。
刚才我们讲了框架的一个部分,它发生在我们的治疗室中、发生在你的办公室里。这个框架的第二个部分是来访者需要坐在他们的椅子上。如果来访者站起来了,在这个治疗室里开始来回地走动,这也是对框架的一个打破。
这也在我的一次治疗中发生的,在治疗中段的时候,这个中年男子就站起来来回走。我想明白他为什么要来回走。他说,我就是觉得紧张。但是那一节结束之后,他给我打电话,取消了接下来的治疗。之后,我才明白,他当时站起来其实是一种象征意义的表达。实际上,他整个人是想走出我的治疗室、走出我的治疗。然而,当时我没有来得及跟他讨论这些内容。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发现来访者不管是对治疗还是对你有这种负向情感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地帮他去言语、去表达这种或苛责的、或愤怒的态度。这样的话,可以使得来访者继续留在治疗里。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倾向于见诸行动、放弃治疗。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治疗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治疗的目标,我们是希望有一天来访者能够弄清楚自己的问题,不需要治疗了,结束治疗。治疗的目标永远不是把来访者留在治疗里的。
我们为什么在这还要去讨论这些技术呢?就是我们怎么去设定这样一个框架,我们怎么去注意到来访者对于框架的这些打破,然后去注意到来访者想要放弃治疗的这些冲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说,他所有试图去打破我们这个治疗性框架以及我们这种治疗性联盟的那些力量,其实是基于某种情感的,他基于这种情感开始见诸行动了。然而,这种情感通常是被他遗忘的,可能是跟他过去父母的冲突相关的那些感受。而那些感受带来了当今他现在的那些问题。
我还有一个案例。这是一位40来岁的亚洲裔男性,现在在美国工作。他来的原因是他抑郁。然后他来了就说他抑郁。我跟他说,那和我讲一讲吧。他说,你问我个问题吧。我说,有意思呀,你想让我问问题?他说,你年长嘛,我很尊重你,我就会在这里等着呀。如果你问问题,我会很服从地(回答你)。就是你问什么,我都会回答的。
当然,一方面我理解,我也指出说,这个可能在他自身的文化中是正常的一个表现。然而,他同时也向我展现出他非常被动性的一面,他被动到连描述自己的问题都非常得困难。我这么说完,他立马回应到说,哇,我老婆也是这么讲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讨论了他和他妻子之间,他自己被动性的这个部分。他从来不问他妻子问题。他从来不会问她说,你过得怎么样?我们慢慢发现,这是他的一个人格特质,跟他的童年经历有关系。因为他小的时候,每次问他妈妈问题,他妈妈都会打他。另外一方面,他非常爱自己的父亲,并不想失去他的爸爸。但每一次试图去挑战他父亲的时候,他总是害怕,担心失去他父亲。他的这种恐惧也是引起他被动性的另外一个面向。
很有意思,因为我既不是他妈妈,也不是他爸爸,他为什么对我还是这么被动呢?而且他不仅是对我被动,他对他的妻子,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人,他还是这种非常被动的人格特质。换而言之,当我对这一内容进行分析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移情分析。我们去分析他对我的这个移情性情感。这部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且对他的人格做出进一步的改变。
我还跟另外一位55岁的女性一起工作。她的问题在于她有惊恐发作。一段时间之后,她的问题有所改善。当然,她对我的感受也很好。她就跟我说,Blackman医生,我可以抱抱您吗?我说,不行,因为我们的关系并不包含拥抱这个部分。但我在想,会不会是你想通过这个拥抱来表达你很开心或者对我很感谢的这些情感?她说,你让我说这些话也行,但我总感觉跟抱你感觉不太一样。
那我们基于此,进一步地就去讨论她那个非常冷漠的、酗酒成瘾的母亲,在她童年的时候几乎很少去抱她。实际上,她特定的想要拥抱我的这个想法,跟她自身的惊恐发作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当我跟她说不行的时候,她觉得非常的内疚、非常的羞耻。然后她说,抱歉,抱歉,我不应该说这个事儿。
接下来,我们基于这一内容进一步地去澄清,当她开始有一种强烈的想要去拥抱别人的冲动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在拥抱的这个冲动里,它实际上是有一些跟性相关的特征。在这样冲动的情感下、这些强烈的冲动里,她一方面就会觉得,我好丢脸呀,因为我把我这个部分暴露出来了。同时,她还会觉得,因为别人拒绝我了,还是会让她觉得非常的羞耻。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会怎么做。来访者给你发了一个很长的信息,这个信息无关于咨询预约的部分,而是非常充满意义的。在他和你上一次见面之后,发了一些进一步的想法。我们生活在21世纪,大家经常发信息。我会做什么呢?不管他是发微信给我,还是发信息给我,我通常会说,收到了,期待下次见面和您继续讨论。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不回信息的话,不太礼貌。但另外一方面,我也不想来访者去打破这个工作框架,在治疗室之外进行这种非常重要的讨论。
总结一下,在刚才这一段内容里,我们去讲述了由Robert Langs提出的工作框架这一个概念。当我们讲到治疗性框架的时候,它首先需要发生在治疗室中,需要来访者坐在他的椅子上。当这一个框架开始被打破的时候,它就提供了我们可以去进行进一步诠释的一些素材。这些素材可能会包括一些移情的内容。
好多年前,我当时还在受训中,我的督导超有幽默感。他说,理论上,如果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情境:你的来访者从你的窗户里跳出去了,那在他落地前的那一刻,你一定要问他一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然了,如果这事儿真发生的时候,你可千万得先拽住他。之所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当来访者去打破这个治疗框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试着去理解这种打破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03.关于治疗联盟
现在让我们进入到更为有趣的、也更为复杂的这个部分。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理论家Elizabeth Zetzel,她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著名的一位精神分析理论家。她进一步去阐述了和治疗师之间的这个关系。她指出说,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或者方式来看待这个关系,她把它称之为治疗联盟。这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工作联盟和框架是不同的概念。这种(类型的关系)特指是那些在治疗中一切进展良好的、跟你的治疗关系也是很好的、每次跟你工作完之后好像都会有更深的(进步)的类型。
我们接下来看第一点。比如,我们经常说来访者想要放弃治疗,你就可以向他指出或者帮他一起试图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跟自己的治疗师对着干呢?这就是来访者对你诠释阻抗的一个反应。这个时候,如果来访者可以对此了解更多的话,他可以进一步地和你加深这个合作性的关系。
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这样一位女性。她的父母都离世了,给她留下了巨额的遗产。但她对于这些钱非常得内疚,没有办法去花掉它们。两三次治疗之后,她跟我说,我觉得我付不起你的治疗费了。我接着回应她说,我觉得你的意思是,你并不想用你遗产中的任何部分来付你的治疗费,因为你觉得太内疚了,你完全没有办法花这部分钱。当我跟她指出这个部分的时候,她开始哭泣了。她跟我讲,如果她真的动用这笔钱,就像她去承认她妈妈真的已经去世一样。
她同意接下来接受治疗。下一节治疗的时候,她跟我说,我给我姐打过电话了,我征得了她的许可,我可以花这笔钱来付您的治疗费。我们在这能够理解到,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丧失本身,还有一些对于使用这笔钱的内疚感觉。她觉得如此的内疚,所以她不得不需要事先争取她姐姐的许可。当我们进一步去讨论她的这个内疚的感受时,她接着说,当她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她总是跟她妈吵架,她总是对她妈特别特别生气。
在我们对这一内容进行讨论完之后,她很有兴趣继续见我,而且一周两次。在那之后,她再也没有说想要终止治疗。换而言之,她实际上针对我对她的这个阻抗意义的诠释或者澄清做出了一个反应。她这个反应就是说,我不再坚持说我要放弃治疗了。基于我前面对于她这种阻抗,我进行了一个诠释和澄清。
当你跟来访者之间工作可以发展出很好的治疗联盟的时候,你压根儿就不需要问他那么多的问题。之所以你不需要问那么多问题就能工作的原因在于,当你开始能够跟来访者发展出这种治疗联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们两个之间形成了,或者来访者对你形成了一种基本的信任。
我有一个35岁的女士来访者非常的害羞。有一次治疗结束的时候跟我说,我有一个梦,但我不想跟你说。我就直接问她说,这跟信任有关系吗?她说,不是那么回事儿,Blackman医生,我非常信任您。我就是觉得太丢人了。我就接着说,好像这就是你在大部分感觉到丢脸的时候,会做的事情,你会开始变得沉默,你也不告诉别人你在想什么。她说,好吧,跟你讲一下吧。在梦里,她梦见她跟我在一起,在一个汽车旅馆里,我们俩一起在做爱。
我们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来分析这个梦,因为这个梦中有好多层的意义。第一层意义是,她把她对于她现在男朋友的一些情感移植到我的身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她的想象是,她如果能跟我发生性关系,她就不会失去我。这个部分和她儿童时期非常抑郁的一个情感相关,因为她的父亲在另外一个城市居住,她几乎很少能见到他。
在这最重要的是,她能够参与到跟我的工作中进行自由联想,向我报告她的梦,能够进一步去分析她的梦,进一步去理解她的这种羞耻的感受,并且有所改善。在这个治疗结束之后,她自己回去接着思考,她说她总是觉得很丢脸。丢人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真的跟性相关的那些幻想,而是她小的时候是非常渴望跟她的父亲结婚的。当她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对于和男人相处的那种非常不安和害羞的感觉有很大的缓解,几乎消失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其实这个内容会反复地出现。她会说,你知道吗,我又碰到了一个不错的男人,但是我觉得好害羞啊。我知道你一定知道原因吧。因为我其实对他有性幻想。你也知道为什么吧?因为我这个性幻想,小的时候是朝向我爸爸的。所以我就什么话也没有办法跟她讲。整个这个过程,你能看到这个来访者开始独立地进行这种自我分析。
也就是说,当治疗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如果你对来访者的阻抗进行诠释,来访者是可以做出进一步响应的,这就会增强你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来访者能够开始进行某种自由联想,她也能够发展出和你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信任感觉。她能够自己进一步地去结合一些新的材料,最终能够进行独立的自我分析。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人就想跟我争辩了,那你说那些边缘性人格组织的来访者怎么办?他几年都不一定能信任你。当然我们知道,当讲到边缘性来访者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有早年的童年创伤,这些童年创伤通常都是与分离有关的。对于他们而言,可能信任任何人都成问题。
在这跟大家介绍一条基本的一般性原则。这条技术性原则是什么呢?当你发现来访者开始去打破或者中断这个工作性联盟,开始去打破这个治疗性框架,如果你觉得你们之间的这种治疗性联盟实际上是存在某种失误的,那这些问题需要被优先处理,也就意味着这是你最先要去干预的部分。
这个原则有两个例外。第一个例外就是,来访者如果是自杀性的,那我们首先要先处理他的自杀问题。第二个例外就是,你发现来访者准备卷入到某种非常危险的行为之中的时候。在这两个例外的情况下,我们是不管什么联盟的。这个时候,我们试着让来访者理解他指向自己的那些暴怒的情感,比如说来访者有这种自杀性的一些尝试行为和想法的时候。
刚才我们说,我们先把联盟放到一边,帮助来访者去理解他们朝向自己的暴怒。或者第二种情况,就是来访者卷入到这种危险行为的时候,我们要让来访者看到他自己的否认,他并没有去看到真正的现实的危险部分。
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例外,就是排除1和2,我们第3个就是要直接去干预来访者对于各种框架的一个中断或者是一个打破。这种对于框架中断的干预或者是诠释,一定要优先于对来访者问题材料的工作和理解。
我们讲最后一个部分,看看当出问题的时候,问题有哪些不同的表现方式。这里有一部分是和治疗师自己的错误有关的。这些错误,要么导致治疗师进一步的危险性行为,要么直接就引发来访者放弃治疗。
其实有一件特诡异或者特奇怪的事儿。我看了50来年的电影,我发现只要这个电影里有一个治疗师,这个治疗师一定会打破框架。而且如果他不和这个来访者直接发生性关系,他一定会和这个来访者家庭的某个成员发生性关系。美国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就是在所有的这些专业人士中,其中有3%的人和他们的来访者、他们的病人发生性关系。当然,我们会觉得3%是很小的一个数字。
接下来我们看,这是一个电影的剧照,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潮浪王子》,讲这个男人实际上居住在大海之上。在这个电影里,这个男主角的妹妹心理上有很多的问题。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妹妹的治疗师,是非常著名的女演员Barbra Streisand。然后整个剧的故事就是说,我们的男主角(由NickNolte扮演)因为妹妹生病了,就来看看妹妹到底发生了什么,最终卷入到和妹妹的治疗师的性关系中。
我还记得另外一个剧《The Sopranos》,大概在10年前、12年前播放的。是一个讲黑手党的影视剧。黑手党的这个党首,他有惊恐发作,我觉得那个症状在他的身上看起来不太合理。然后这个党首就去找了一个女性治疗师看病,最终跟她发生性关系了。
我这辈子唯一看过的一个把治疗师描绘得还算正面形象的电影,是上世纪60年代的,那个电影叫做《总统的精神医生》,其实看起来挺有意思的。即便在这么一个正面的治疗师的电影之中,还是有治疗师对于框架的一个打破。我们讲,伟大的总统先生觉得我需要治疗了,然后他就雇了一个分析家,是由James Coburn扮演的。治疗师是送治疗上门的,就是直接到白宫去给总统提供心理治疗,而且是随时,只要是总统想,然后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治疗。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一旦发生对这种治疗框架的打破的时候,我们要去谈论这个部分,要去工作这个部分,毕竟我们是谈话治疗。如果来访者迟到了,或者不跟你说话,自己在那里忙别的,你不去讨论这些部分,其一,你失去了一个进一步理解来访者的机会;其二,其实这样,你已经放任进一步的糟糕的结果的发生。
这让我想起了在45年前,我当时刚刚开始个人执业,一个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说跟自己的男朋友之间有一些问题,想来治疗。我就给她约了一个时间,告诉她我的治疗费。她在我的治疗室中坐下来之后,她直接跟我讲,我实际上是一个妓女。她说她之前确实有个男朋友,但是他们分手了,她现在正在找新男朋友。我看了你一眼,我觉得你可以成为我新的男朋友。
为了向我证明她是一个好女友,她跟我说,我可以在你的办公室跟你发生性关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太好的事儿,因为当你试着跟我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相当于你就摧毁了我作为你医生的这个角色。你也在邀请我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我觉得背后的原因也许在于因为你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也许邀请我参与其中,会让你觉得这一切没有问题,你不需要因此而担忧。
我接着讲说,第三点,也许你不断地想向自我证明,爱并不存在,性只和钱有关。所以我跟她说,我什么都不会对你做的,但是我愿意跟你继续讨论我刚才提到的所有关于你的这些问题。然后她对我笑了一会儿说,你还挺不错的。她付了本次的费用。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给你们的这个例子,就想让大家看到,一个人是如何试图去打破这个框架,如何试图去打破这种治疗性甚至工作性的这个联盟的。
04.治疗师的失误操作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些治疗师会犯的典型性错误。其一,治疗师会允许来访者迟到,而且还不去进行相关讨论。或者他们允许来访者几周甚至是几个月不付费。如果治疗被用作其他用途,治疗本身就不会存在。
我督导过很多类似的这样个案,就是治疗师跟来访者都工作一年多了,但是找不到任何来访者的主诉。可能在治疗师眼中,来访者有很多的问题,但好像病人并不愿意去接受说这是我想进一步去工作的点。
还有,我之前也提到了,有个来访者来的时候只为了去取悦于别人,就是治疗之外的第三方。如果来访者来见你只不过是因为他妈妈让他来,那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和来访者之间形成治疗性同盟。如果这个情形真的发生在你的治疗室中,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问这个来访者,那你呢?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或者你就直接说,有意思呀,好像你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但你是个成人了,你又不是一个孩子。
这其实还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因为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来了会直接就告诉你说,我来见你是为了让别人高兴。
我督导过一个中国治疗师的个案,他说他的来访者是一个25岁刚刚经历过流产的女性。虽然来访者确实因为失去这个胎儿感觉到非常抑郁,但来访者来治疗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来访者的母亲告诉她说你要去治疗。
当然,这个流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一定是有一个很长的故事的。这个故事就是,她在约会交男朋友,突然间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还挺爱她男朋友的,然后就决定说我们结婚,养这个孩子吧。然后男友就登门拜访了这个女孩的母亲。后来女孩的妈妈说,你不能跟这个人结婚,他太矮了。
听到这,我觉得这个妈妈还是挺(精神)紊乱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她压根儿不关注这个男人的人格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不是负责任的、能不能承担起作为丈夫的责任,工作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对女儿好不好。这些她都不关心。她直接看到的就是这个男人到底有多高。
听起来,来访者也没有去想我刚才想的那些问题。但是她还是试着跟自己的妈妈争辩了一下,她说,妈,他可能是挺矮的,但是我怀孕了。她妈说,我不管,把孩子流产吧。女儿接着说,那我会非常难过的,我不想去流产。她妈说,如果你难过,你就看治疗师好了。在那之后,女孩子就去流掉了这个孩子,然后接着去看了治疗师。
我向被督导的治疗师指出,这个可怜的女性,她实际上在使用去分离化的这个防御机制。去分离化意味着,你放弃自我身份认同的部分,因为你害怕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没有办法取悦别人。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治疗师去跟来访者讨论她的这个防御机制。去讨论这个部分,实际上是试图帮助来访者看到自身的问题,看到她自身被动性的这个部分,她实际上不仅仅放弃了自我身份认同的这个部分,还向她残忍的母亲放弃了这个婴儿。
所以在此,我们讲主诉并不一定有意义,真正的问题是她自身的这种被动性和她去分离化的这种防御机制。我们的治疗师在这就要去工作这个部分,帮助来访者看到并且理解到这才是她真正的最大的问题。
最后的时间,我们去讨论一下那些想跟你做交易的来访者。这些来访者想跟你发生一点治疗性联盟或者工作联盟之外的其他的交易。
我有一个来访者抑郁了好多年,他老婆也不断地抱怨说,你一点都不关注我,你也不在我身上花时间。然后来访者说,我知道我确实有这些问题,但我并不想去改。他说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其他人还需要我呢,我老婆太自私了。他继续进一步向我解释说,我有一个妹妹,她经济上有很多问题,我得帮她。我还有一个弟弟,他自己有一个修车厂,我有的时候还会过去帮他修车。他还给我举了好几个例子,都是说他一直要帮别人去修一些什么东西。
在我听完他整个故事之后,我就向他指出,我感觉你好像有一种强迫性的这样一个部分:就是想要帮别人修什么东西。这是不是因为你并不想把自己放置到那种需要别人的位置上?来访者回答说,我觉得你是对的,我觉得你非常可能是对的。这样说起来,很像我爸,我爸总是帮着自己家里那些人,并不是真正地关心我,也不关心我妈妈。
然后第二次治疗,他来以后跟我说,您真的太有帮助了。我觉得您帮我意识到我确实像我爸爸一样。我假装我自己并不需要别人照顾我。我上次回去之后,我就跟我妻子讨论了这一点。她给我做了晚餐,我们在一起交谈了好几个小时。我觉得感觉好多了。
然后他接着说,我觉得您应该写一本书,就把我这个例子写出来,就是写我这种总是想修东西的人。我可以给你找一些出版商。我认识很多人的,一定会让你赚好多钱。我想一定会大赚一笔,然后我也可以在其中拿一点。
这个时候,你大概能够理解到为什么我们说工作联盟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此基于工作联盟这个概念,你才能够发现他想在联盟框架之外跟我进行某种交易。当然,我当时很容易就说,这个提议还挺有意思的,你现在对我做的事情好像跟你对别人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好像你感觉到你也需要修理好我的问题。他说,噢,您说得对,但咱们可以大赚一笔呀。我说,没问题,只要你理解到你的问题了,然后你按时给我付费,对我来说,这个钱就够了。
实际上,也许存在着几千种不同的方式来扰动你和来访者之间签订的非常简单的合约。可能每隔一段时间,你都会觉得要不要给这个原则找一些例外。但即便外面有这么多的冲击、这么多例外的可能性,只要我们具有这种结构化的工作性联盟,或者我们讲框架,或者治疗性联盟的这样一些观点。当来访者开始试图去打破这个框架,或者去建构一些假的联盟的时候,你就开始能够注意到,并且你可以把这个部分带到来访者的面前,让他开始去关注,并且进一步去理解这背后的那些内容。
(本文内容为厦门朴生心理原创,版权归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所有。
转载请联系15859242450,并注明出处。)
预约咨询请添加助理微信

编辑: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