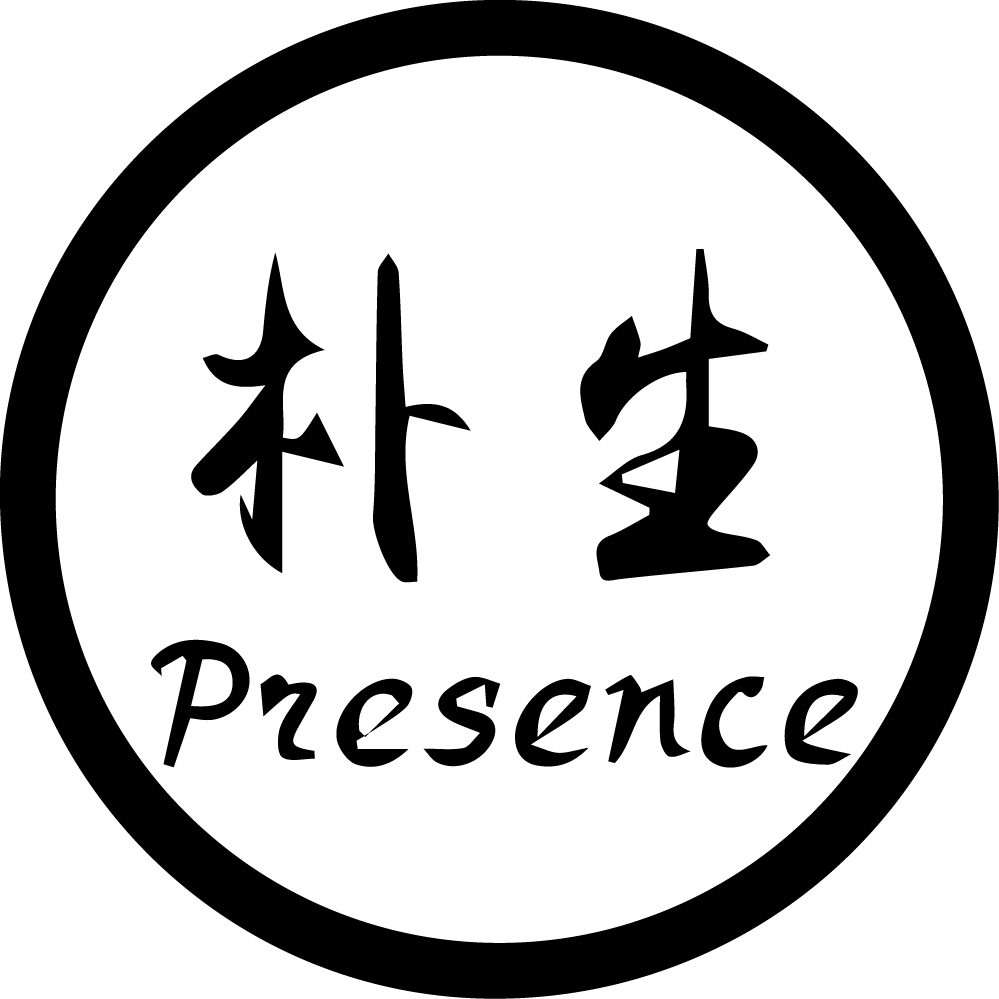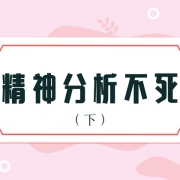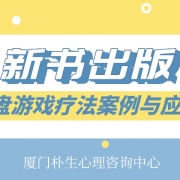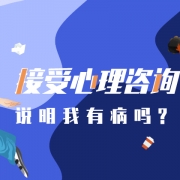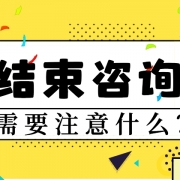医患关系背后的心理动力


写在前面
“孙文斌杀医事件”一发生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据统计,此次杀医事件是我国近十年来,近300例伤医事件之中,性质最为恶劣、发生过程最为残忍的伤医事件,这掀起了人们持续至今、夜以继日的关注与愤慨。
从目前已知的报道中,我们不应该把此次事件列为“医患纠纷”,把它视作一起性质残暴、令人发指的恶性谋杀事件也许更为准确。因此,下文所讨论的“医患关系”也未必能完全适用于对这种极端情况的理解。
我们想做的,只是在强烈的触动之余,试图从专业的角度去思考:为何医患关系的激化,无论对医生或患者而言,都是一件极为令人哀痛的事情。

医患关系,是母婴关系的一种再现。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和治疗,这跟我们小时候寻求自己妈妈的帮助和庇护的情景极为相似。
在我们生命最初那些日子里,因为身体发育条件的限制,我们的食物、水、温暖这些维持生命存在和成长必须的东西,大都来源于母亲。也就是说,小时候我们“衣来张口,饭来伸手”;
等长大成人,生病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选择向医生寻求帮助,听医嘱、按照医生的处方服药或接受治疗,让医生帮助我们解决身体病症,同样是一种象征层面的“衣来张口,饭来伸手”。可以说,患者跟医生的关系,像极了我们曾经跟自己妈妈的关系。
医患矛盾的激化,是一种退行性暴怒。
既然医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母婴关系,那我们对自己妈妈的那些爱恨情仇,同样也会倾注到医生身上去。
在我们生命早年,妈妈是食物的提供者,是我们温暖的港湾,弱小的我们都会把自己的妈妈想象成是无所不能的、充满力量的,甚至是神一般的存在,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感到基本的安全和自在。可一旦我们幼小心灵发出的需求没有被及时的满足,妈妈那光辉、伟大的形象瞬间会崩塌,“好妈妈”会被我们理解成糟糕的“坏妈妈”形象。
类似的,当医生可以为我们缓解病痛、解决问题时,他们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位“好妈妈”形象;而一旦一些病症连医生无能为力或医生暂时还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早年那个“坏妈妈”的形象就会跃然而出,一股脑的倾注到医生身上。▷▷全能理想化——“你不是医生吗?你就应该什么都会治啊!”
▷▷否认(不接受病情不接受死亡)——“她就是被你们给致死的”
▷▷恶意贬低——“这个病都治不好?你算是个什么医生!”
▷▷攻击行为——辱骂/身体伤害/残忍杀害
在这次的“孙文斌杀医事件”中,杨文医生的同事回忆起孙文斌在得知家人病情的原话是:“我妈要是还不退烧,就把大夫给弄死”;对医生残忍的行凶,也像极了原始自恋受损时的暴怒——那种要将对方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抹杀掉的疯狂冲动:“杨文医生躺在抢救床上,满身是血,颈部有多处刀伤,其中一刀砍断了右侧颈全部肌肉,砍断了食管、气管、颈内静脉、颈总动脉,和通往身体的神经,连颈椎骨都断了。”

作为医生,满足患者作为“真实的人”的那些需求
在医院接受治疗和帮助的患者,除了正在经受疾病痛苦,他们往往还具有着一些内在的、不易发觉的心理体验。
▷▷ 人与人之间的影响是通过潜意识作用的▷▷ 医护人员工作性质要超纯理性和习惯性的情感隔离;要让医生返回人的本性
▷▷ 患者除了治病的需求还有其他的心理需求
▷▷ 医生面对的不只是患者,而是患者的整个家庭
▷▷ 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移情,父性和母性移情
在小组中,大家为了达成上述共识,会经常涉及到以下这些主题:
▷▷疾病导致生死的分离问题
▷▷疾病导致自我价值和尊严
▷▷疾病导致身体缺失
▷▷疾病所引发的家庭纠纷
▷▷疾病引发的羞耻感和内疚感
▷▷长期医护工作对自己的心理影响
这些都会帮助医护工作者们训练自己的觉察力和反省力、提升自己的共情能力,这些都会对缓解医患矛盾,促进医患关系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作为患者,破除对医生那些“神化”的期待
我们对于自己心中那位“全能的妈妈”,总会抱有一些理想化的幻想和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医院是见证生离死别的场所,所以医生正好也是救死扶伤、“挽狂澜于既倒”的一种特殊的职业,所以他们便是最容易被投注为“全能”、甚至是很容易被神话的一个职业。然而医生,只是一种职业而已,充其量算是经过多年专业化学习和训练的专业人士罢了。而且,医生首先是作为活生生的人而存在,他们有着自己七情六欲,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困扰和能力极限。医生的这份职业,是被训练来救死扶伤的,但并不表明他们就是非得是无所不能的,一定就得有起死回生的魔法。人世间唯一无所不能的,只能是我们头脑中的幻象,所以对于患者来说,求医问诊最好的态度就是:充满希望,但接受现实。
参考文献
[1] 海德·奥登.职业化关系:巴林特小组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5-06-01.
[2] 张辉,方晟宇,杨凤池.从精神分析视角剖析医患关系[J].中国医药导报,2015,5,14.
(本文系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原创内容,未经允许严禁转载。转载请联系15859242450)
预约咨询请添加助理微信

编辑: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