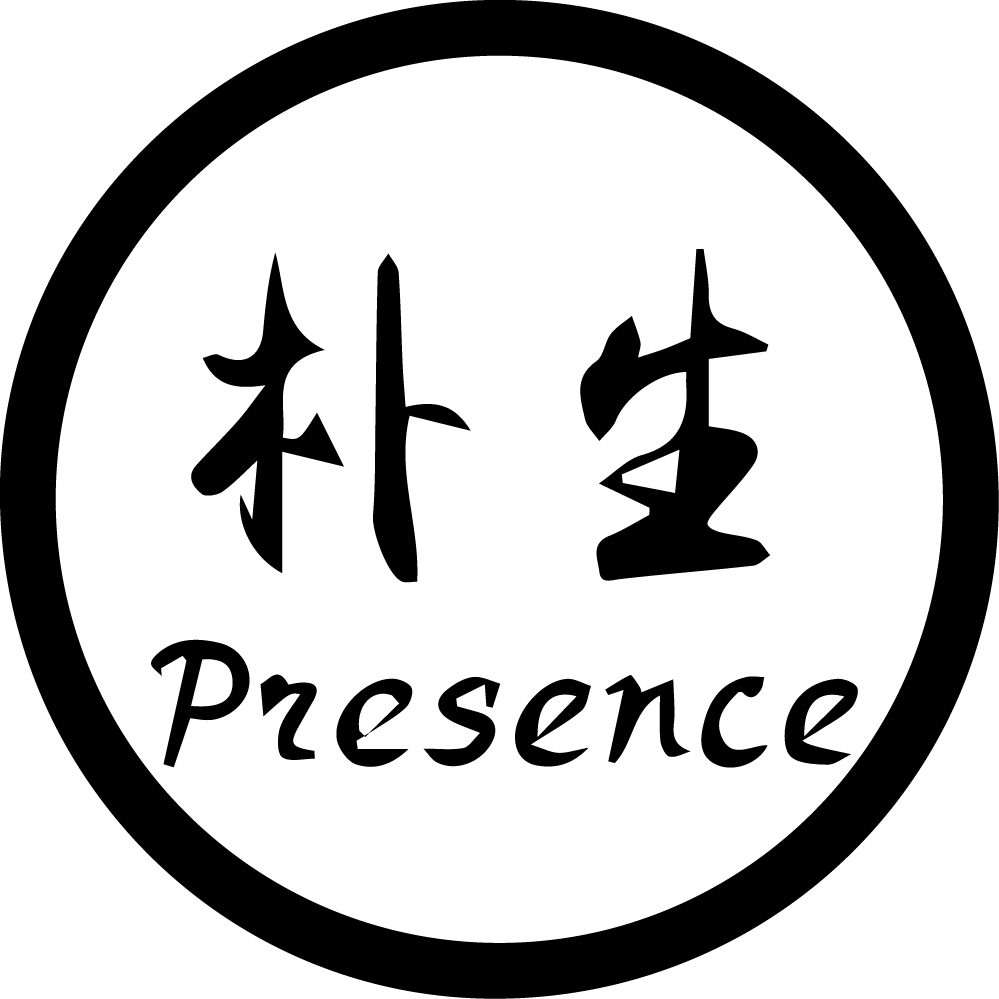梦,我们理解心灵的语言
原文:C.G.Jung
编译: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
我们不只把梦视为智力的运作,而是把梦当成一种能够用以揭示无意识心理内容的方法。而这些无意识心理内容正是心理问题的成因,对疗愈心理疾病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C.G.Jung
象征,对意识的超越
人类会使用口语或者书面语来表达自己想要传达的意思。人类的语言中充满了象征,但也经常运用一些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描述性内容的符号和图像,它们其中有些是缩写或者一些单词首字母的大写组合,例如,UN(联合国)、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些是人们所熟悉的商标、专利药品名称、徽章或者标志。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意义,它们通过常见的使用方法或特定目的而获得了大家公认的含义。但这些东西并非象征,它们只是符号而已,除了表示它们所代表的对象之外,再无其他。
我们所称作的象征是一个术语、一个名称,或者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画面,其除了传统和明显的意义之外,还有特定的内涵。对我们而言,它意味着一些模糊、未知的或者隐藏的内容。比如,希腊克里特岛上的许多遗迹都刻有双锛图案,这是一个我们知道的东西,但我们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它的象征意涵。再举一例,曾有个印第安人到英国旅游归来之后,跟他家乡的朋友说英国人崇拜动物,因为他在老教堂里看到了鹰、狮子和公牛。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些动物是其实福音传道者的象征,来自以西结的异象,而这些意象又和埃及太阳神荷鲁斯(Horus)以及他的4个儿子有相似之处。此外,诸如轮子和十字的物体遍布世界各地,但它们只在特定的情境下才有象征的意义。准确地说,它们象征什么仍是有争议的推测。
因此,当一个词或者一个意象所暗示的内容超出其明显和直接的意义时,那么它就具有象征的含义。它拥有更加广阔的“无意识”一面,其从未被精确地定义或完整地解释。当理智开始探索这个象征的时候,它会带来超出理性理解范围的想法。比如,轮子会把我们的思想引向“神圣的”太阳的概念,但在这一点上,理性要承认自己的无能,人类无法定义一个“神圣的”存在。尽管我们的理智存在局限,但当我们称某种东西为“神圣”的时候,我们只是为其命名,这个名字可能是基于某个信条,但绝非基于实际的证据。
由于有无数事物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因此我们要经常使用象征的术语来表示我们无法定义或者无法完全理解的概念。这就是所有宗教都会使用象征的语言或者意象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在意识层面地使用象征,它仅仅是无比重要的心理事实的一个面向:人类同时也在无意识地、自发地以梦的形式产生象征。
要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如果我们想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人类内心世界的运作方式就必须理解这一点。只需稍做思考我们就会明白,人类是不可能完整地感知或者完全理解这世间任何一种事物的。人能看、能听、能摸、能尝,但能看多远,能听多清,能从触摸中感触到什么,以及品尝到什么样的味道,这都取决于自己的感官的具体情况,而这些限制了人对周围世界的感知。通过使用一些科学仪器,人可以部分地弥补自己感官上的缺陷,比如,人可以通过望远镜来扩大视野范围,或者借助电子放大器扩大听力范围,但是哪怕最精密的仪器也只能把远处或者小的物体带到其视野范围,或者让微弱的声音听起来更清晰一些。无论我们使用什么工具(即便是AI科技),它都会在某一时刻或某一点到达确定性的边缘,而超过这一点,有意识的知识便无法到达了。
此外,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还有无意识的方面。首先,即使我们的感官对真实的现象、景象和声音做出反应,它们也会以某种方式从现实的世界转人内心世界。进入内心之后,它们就成为心理事实,而其根本的性质是不可知的(因为心灵无法知道它自己的精神实质)。因此,每一种经验都包含无限多的未知因素,更不必说每一个具体对象在某些方面都是未知的,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事物自身的根本性质。
梦,一种象征的语言
然后,还有一些事情超出了我们意识层面的觉知,可以说,它们一直处在意识的阈限之下。它们已经发生,但只是被下意识地吸收了,而我们的意识并未注意到。我们只有在某个直觉的瞬间,或者通过深思的过程,才能意识到这些事情的发生。而且是在这个直觉的瞬间或在深思的过程之后,我们才发现它们一定发生过——尽管最初我们可能忽略了它们在情感和事实上的重要性,但后来,这种重要性会以某种事后想法的形式从无意识中涌现出来。
比如,这些部分会以梦的形式出现。一般来说,任何事件的无意识面向都会通过梦呈现出来,但它在梦中并非一种理性的思想,而是会以一种象征的意象来表达。在历史上,对梦的研究最先使心理学家们能够探索有意识心理事件的无意识面向。
心理学家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证据而假设无意识心理的存在——尽管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否认它的存在。这些反对者天真地认为,做这样的假设就暗示了两个“主体”的存在,或者是同一个个体内存在的两种人格。但这正是它所包含的意思,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现代人的诸多诅咒之一,很多人饱受这种分裂的人格之苦。但这绝不是一种病理性的精神症状,而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看到的正常现象:自己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这绝不仅仅是受精神问题困扰之人的特例。这种困境是一种普遍的无意识现象,不可否认的是,无意识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
人类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缓慢又艰辛的过程,在经历数不清的岁月之后才达到今天的文明状态(粗略地讲,这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4000 年文字的发明)这一进化远未完成,因为人类心灵世界的大部分领域仍然处在黑暗之中,我们所理解的“心灵”绝不单单等同于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内容。
否认无意识存在的人实际上是在假设我们现在对心灵的认识就已经是全部,很明显这个信念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我们假设自己知道自然宇宙的一切一样。我们的心灵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拥有无限的神奇奥秘。因此我们既不能彻底定义心灵,也无法完整地定义大自然。我们只能陈述我们认为它们可能是什么,并尽我们所能地描述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因此,撇开医学探究所积累的那些证据不谈,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反驳“无意识并不存在”这样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是表达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厌新主义,其本质上是对新生事物的恐惧。
这种对人类心灵中未知部分的思想所产生的抗拒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们人类的意识是大自然中最新近的产物,它仍处于“实验”的状态。它十分的脆弱,会受到一些危险的攻击,容易受伤。正如人类学家所指出的,原始人中最常见的精神失常之一就是他们所称作的“灵魂的丧失”——顾名思义,就是明显的意识分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精神解离)。
这些原始人的意识发展水平和我们的不一样,“灵魂(或心灵)”在当时并没有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合体。很多原始人认为,世间万物都和他自己一样,都有一个“丛林灵魂”,这个灵魂会化身为一个动物或者一棵树,人类个体与之具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结。这就是著名的法国民族学家吕西安·莱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ǔhl)所称的“神秘互渗”(mystical participation)现象。后来迫于负面舆论的压力,布吕尔不得不收回了这一概念,但我认为他的批评者们错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心理事实,即个体可能会拥有与其他人或物体相同的无意识身份。
这个身份在原始人中有很多种形式。如果丛林灵魂是动物的灵魂,那么动物便被视为人类的兄弟手足。例如,如果一个人的兄弟是鳄鱼,那他在鳄鱼出没的河里游泳就会安然无恙。如果丛林灵魂是一棵树,那么这棵树便被认为对与之相关的个体具有类似于父母般的权威。在这两种情况下,可以将对丛林灵魂的伤害解释为对人的伤害。
在一些原始部落里,人们认为一个人可以拥有许多个不同的灵魂。这种信念表达了一些原始个体的感受,即他们每个人都是由几个彼此相互联系但又截然不同的部分所构成的。这意味着个体的心灵远非统一、巩固的整合体;相反,在强烈、失控情绪的冲击之下,心灵很容易就会产生分裂。虽然我们是通过人类学家的研究了解这种情况,但它与我们自己的先进文明之间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毫不相干。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进入解离的状态,失去自我认同感。我们可能会被情绪控制和改变,或者变得不可理喻,不能回忆起与自己或他人有关的一些重要事实,因此,人们会问:“你被什么魔鬼附体了?”我们会说能够“控制自己”,但自控是一种非常罕见又非凡的能力。或许我们会觉得自己完全能够实现自控,然而,身边的朋友可以很容易地道出一些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内容。
毫无疑问即使在我们所谓的高度文明之中,人类意识也尚未发展到理想的那种连续、稳定的水平。它仍然很脆弱,并且有解体的风险。这种能够独立分离出一部分思维的能力的确是一种可贵的特质,它使我们能够一次只专注于一件事情,同时把其他需要我们注意的内容排除在外。但是,有意识地分裂与暂时压抑心灵中的某一部分,或是这种情形在某种情况下自然发生,而没有被个人知情或同意,甚至违背个人意愿,这两种情况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前者是文明发展的成就,后者是原始的“丧失灵魂”的情况,甚至是心理问题的病理原因。
因此,即使是在当今世界,意识的统一体依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它太容易遭到破坏了。因此,从一个角度看,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可能是非常理想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能力是一项令人怀疑的成就,因为它会剥夺社会交往中的多姿多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必须重新审视梦的重要作用,即审视那些脆弱的、难以捉摸的、不可靠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幻想的重要意义。为了解释我的观点,我想描述一下它是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出来的,以及我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梦,它是理解人类心灵象征功能的最常见和最普遍的素材。
症状,对无意识内容的表达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最早从经验的角度对意识的无意识背景进行探索的先驱,他研究一个普遍的假设,即梦并非纯粹偶然的现象,而是和意识的思想和问题有关系。这个假设一点都不武断,它建立在一些著名神经病理学家[如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即神经症状与一些意识的经验有关,它们甚至似乎是意识心理的分裂区域,其在其他时间和不同的条件下,可以是意识的。
20世纪初之前,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Breuer)已经认识到精神疾病的症状——歇斯底里、某些疼痛障碍以及一些异常行为——实际上具有其象征层面的意义。它们是无意识心理的一种自我表达形式,就像在梦中一样,这些症状都有象征的意涵。例如,当一个病人在面临难以忍受的状况时,他可能会在吞咽的时候发生痉挛:他“无法吞咽”;在类似的心理压力条件下,另一个病人可能会突发哮喘:他“无法呼吸”。第三个人的腿可能会出现特殊的麻痹:他不能走路,也就是说,他“无法迈开步子”;第四个人会在吃东西后出现呕吐,出现一些“无法消化”的状况。我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但以上诸多生理反应只是困扰我们的诸多问题藉由无意识地方式得以呈现的形式。它们也经常在我们的梦中出现。只要听过很多人讲述的梦,任何心理学家就都会知道,梦的象征要比精神疾病的生理症状更加的丰富多彩。它们通常是由一些精心设计、生动形象的幻想构成。但是,如果分析师在面对这些梦的时候使用弗洛伊德所创立“自由联想”技术,他们会发现所有的梦最终都可以被简化为某些基本的模式。这项技术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弗洛伊德能够以梦为起点,探索病人的无意识问题。
弗洛伊德所做的观察简单但极为深刻,即如果鼓励梦者去谈论梦中的意象和心中的想法,在他所说的和刻意省略的内容中,他会露出马脚,同时揭示出疾病的无意识背景。梦者的想法似乎不合理且毫无关联,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看出他在试图回避些什么,在压抑什么不愉快的想法或经历了。无论梦者想要如何掩饰,他所讲的一切都指向自己困境的核心。医生看到了生活中太多阴暗面的东西,所以当他把病人的暗示解释为良心不安的表现时,他讲的基本上都是真的。不幸的是,他最终的发现证实了自己的期望。弗洛伊德曾提出,压抑和愿望实现是梦之象征的明显成因。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明确反对这一理论。
弗洛伊德还特别强调梦是“自由联想”过程的起点。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觉得这是一种误导,没有对在睡眠过程中产生的丰富幻想加以充分的利用。我的一位同事将他在俄罗斯坐火车长途旅行的一段经历告诉我之后,我对此真的开始怀疑了。尽管他不懂当地语言,甚至看不懂西里尔(Cyriic)字母,但他发现当自己在默想那些写有铁路通知的奇怪字母时,他陷入了一种遐想,想象着它们可能的各种含义。
想法接连出现,他在轻松的心情中发现“自由联想”唤起了很多旧时的回忆。在这些回忆中,他发现了一些埋藏已久、令人不快的主题,他对此感到大为恼火,这些都是他希望忘记的主题,还有他有意识去忘记的。事实上,他已经形成了心理学家所谓的“情结”,也就是说,被压抑的情感主题会导致持续的心理困扰,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产生精神疾病的各种症状。
这段经历使我体会到,如果想要发现病人的情结,实际上“自由联想”过程的起点并不一定非要是梦。我认为,一个人可以从罗盘上的任何一点到达圆心。我们可以从西里尔字母开始,从对着一个水晶球、转经筒或者一幅现代绘画的冥想开始,甚至从关于一些琐事的日常交谈开始。在这方面,梦和其他的出发点一样,都是同样有用的。然而,梦具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即使它们通常源于某种不安的情绪,其中也会涉及其他习惯性的情结。(习惯性的情结是心理中比较脆弱的点,其对外界刺激或干扰的反应最为迅速。)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联想能够引导我们从任何梦境到关键的秘密思想上。
梦的工作与积极想象
在这一点上,我突然想到可以合理地做出推论,梦有一些特殊且更重要的功能。梦通常有一个清晰且目的明确的的结构,揭示一个潜在的想法或意图——尽管意图往往不能被立刻理解。因此,我开始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关注梦的实际形式和内容,而非让“自由联想”引导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想法到达情结,毕竟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很容易到达。
这一新的理念是我的(分析)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意味着我逐渐放弃了那些远离梦境的联想。我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与梦本身的关联之上,相信梦表所达的是无意识想要传达的一些具体内容。
我对梦的态度的转变也包括如何对梦进行工作方法的改变,这个新的方法可以考虑到梦的所有种种更加广泛的面向。如果是一个由意识头脑所讲述的故事,它会有一个开始、发展和结尾,但梦并非如此。它在时空维度上是不同的。要理解梦,你必须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研究——就像你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物体,你要反复地转动它、摆弄它,直到你熟悉它形状的每一个细节之处。
或许我现在已经讲得够多了,足以表明我是如何越来越不认同弗洛伊德最初使用的“自由”联想技术:我想要尽可能地接近梦的本身,排除它可能唤起的所有不相关的想法和联想。诚然,这些可能会导向病人的各种情结,但我心中有一个比发现导致神经紊乱的情结还要更加远大的目标。对于这些情结,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进行识别。例如,心理学家可以使用字词联想实验来获得他所需要的线索(询问病人对给定的一组单词有什么联想,然后研究他的反应)。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整体人格状况、理解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全貌,那意识到他的梦以及它们的象征意象能起到更大的帮助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有无数各式各样的意象可以象征(或者说以寓言的形式呈现)性行为。通过联想的过程,每一个意象都能使人产生性交的想法,以及导向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关于自己所持性态度的特定情结。但人们也可以通过一套难以辨认的俄文字母上产生的白日梦来发掘这种情结。因此,我提出假设,即梦包含的其实是一些信息,而非性的寓言。之所以如此是有明确的缘由的。这里举例说明这一点。
一位男士可能会梦到自己把钥匙插入锁中,挥舞一根沉重的棍子,或者用攻城槌砸开一扇门。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性的寓言。但无意识出于其自身的目的,选用了其中的一个具体的意象——可能是钥匙、棍子或者攻城槌——这一选择也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而我们真正的任务是要去理解为什么是钥匙而不是棍子,或者是棍子面不是槌。有时候,这会使我们发现它根本不是性行为所代表的内容,而是相当不同的心理意涵。
根据这个推理得我出结论,只有梦中那些明显和清晰的材料才能被用来诠释梦。梦有自己的局限性,它本身的特定形式告诉我们什么属于它,而什么带我们远离它。“自由”联想以某种曲折的方式吸引我们远离那些材料本身,而我使用的方法更像是以梦的画面为中心来不断的绕圈圈,我会围绕着梦中的具体画面来进行工作,同时不理会梦者试图摆脱它的每一次尝试。在心理分析临床工作中,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些话:“让我们回到你的梦中。梦说了什么?’
例如,我的一位病人梦到一个醉醺醺、衣衫不整的粗俗女子。在梦中,这个女子似乎是他的妻子,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妻子的形象与之完全不同。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个梦是非常不真实的,病人立即把它视为胡言乱语而不予理睬。作为他的医生,我如果让他开始一个联想的过程,他将不可避免地尝试摆脱那些他的梦中不好的暗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以一个主要的情结来结束——可能是一个和他的妻子没有任何关系的情结——这样我们就不会了解到这个独特之梦的特定意涵了。
那么,他的无意识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明显不真实的描述来传递什么信息呢?很显然,不管怎么说,它呈现的是有关一个堕落女性的想法,而她与梦者的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但既然把这个意象投射到他的妻子身上不合理,事实上也不真实,那么在我能够发现这个令人厌恶的意象所代表的意义之前,我不得不继续苦苦探寻。
在中世纪,早在生理学家证明我们每个人的腺体结构中都有男性和女性元素之前,就有人说“每个男人的内心重都有一个女人”。我把每一位男性身上的这种女性元素称为“阿尼玛”(anima)。男性心中这种“女性特质”面向,它本质上是一种有关周围环境尤其是面对女性时的自卑,其被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起来,不让外人知道,甚至不让他自己知道。换句话说,尽管个体的外显人格看起来很正常,但他很可能对他人——甚至自己——隐瞒了“内在女性”的可悲处境。
这位病人的情况便是如此:他内在的女性面向并不太好。他的梦实际上在告诉他:“你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像个堕落的女人一样。”这样一来,为什么梦者往往会忽视甚至否认自己的梦所达的信息便很容易理解了:意识自然地抗拒任何无意识的或者未知的东西。我已经指出,在原始人中存在着人类学家所称的“厌新”现象,即对新生事物的一种深刻且迷信的恐惧。这些原始人的反应与野生动物对不幸偶发事件的反应并无差别;而我们“文明人”对新思想的反应也大同小异,他们会在心中设置障碍,以保护自己不受到新事物带来的冲击。这在一个人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想法时,可以很容易观察到。哲学、科学乃至文学领域的许多先驱,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固有的保守主义的受害者。心理学是最年轻的科学之一,它试图研究无意识心理的运作,因此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极端的厌新反应。
参考内容及推荐阅读:
人类与象征.荣格(著),周党伟&林颖(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
寻求灵魂的现代人.荣格(著),徐说(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
本文为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原创内容,转载请联系中心助理15859242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