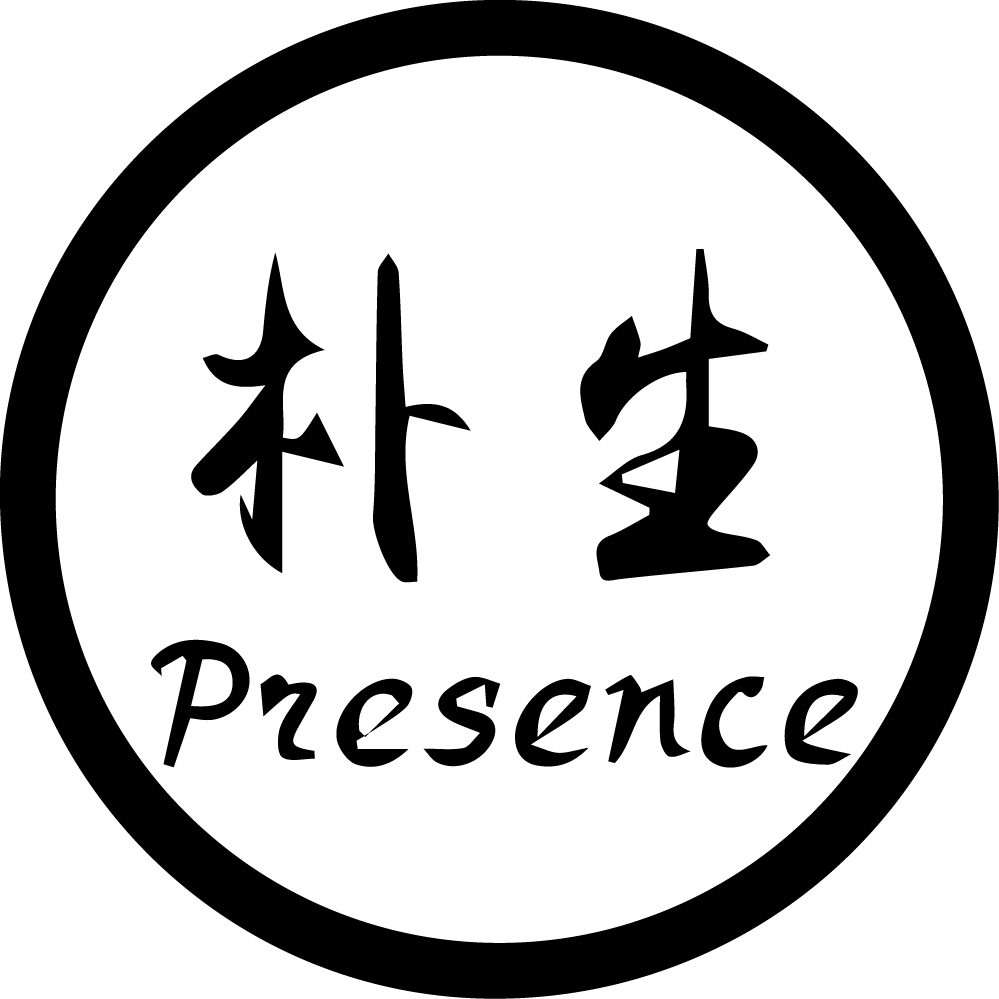作者: Sanford Shapiro, M.D
编译: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 盛文哲

弗洛伊德是一个天才,他发现和病人谈话有治疗作用,他称之为谈话治疗(Talking Cure)。他指出我们自身有一个部分是自己没有觉察,没有意识到的,也就是潜意识。但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谈话带来帮助的原因,后来都人们被认为是不对的。人们在后来发现他对潜意识的理解也不对。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动力来自潜意识中那些被禁止的驱力,被禁止的性的驱力,攻击性的驱力。因为这些是被禁止的,所以我们就很有动力来阻抗它们,来防御它们。弗洛伊德还认为,所有曾经在潜意识中的东西都会通过去除压抑的机制,变得意识化。所有在潜意识中的东西,都曾经在意识中,但继而被压抑了。
然而,为了让这些东西意识化,也要有一些象征性的东西,比如说语言。而语言,是一直要到生命的第二年才会发展出来的。如果你抱起一个两个月的婴儿,你马上就能够分辨出他是喝的奶瓶还是母乳喂养的。怎么分辨呢?就是如果你抱起的这个宝宝是母乳喂养的,他马上就会把头转向你的胸口,而奶瓶喂养的婴儿会把头抬起来。一个一岁大的学步期的婴儿,他在跟妈妈和研究者一起玩耍。当妈妈离开15分钟之后再回来,会出现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是,学步期的婴儿马上就会知道他自己要不要跑,向妈妈张开双臂。第二种呢就是开始发脾气,很易怒。第三就是完全忽视、无视妈妈的存在。这些都是依恋理论当中的发现。这些行为都是没有被婴儿意识到的,但他们也永远不会一直是潜意识的,因为这些从来都没有被压抑过。
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方式是作为一种非意识的记忆编码,存在于大脑当中。非意识不是无意识、潜意识。他们被称为内隐记忆或者程序性记忆。在精神分析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基于这种非意识的或者说内隐的程序性的记忆,而且是我们的洞察或者我们的外显的记忆所触及不到的。
精神分析治疗是怎么发生的呢?弗洛伊德也认为分析的目标是获得洞察——让潜意识意识化。他进一步认为分析师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分析师是病人投射的目标,分析师个人不要参与进去。弗洛伊德认为,袒露分析师个人的观点,或者回答病人向他问的问题会污染治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人心理学,即:出现的所有的内容都只是从病人那里来的。
自体心理学主体间取向分析师史托罗楼发展出了主体间性理论。分析师的场域里不仅有病人的主体性,也有治疗师的主体性。在这个主体间当中,分析性场域中包含了病人在关系中的存在方式,他称之为病人的主体性,以及分析师在关系中的存在方式,即分析师的主体性。在这种模式下,分析发生在这两者不同的主体性之间的界面上。史托罗楼称作主体间的空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二人心理学。
因为很多来访者对他们造成困扰的,是那些非意识的内隐关系。所以病人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告诉我们他们的动力是什么,而必须得要用行为来展现给我们看。这就为移情这个术语赋予了新的意义。每一次成功的分析,病人和分析师都会参与到整个过程当中,重新活化某些早期创伤。关系性的分析师称这个为活化。在一次成功的分析当中,这种活化会被抵消(undoing),会被撤销。那么活化被重新工作之后,这个病人就会在关系上有了一种新的经验。在这种模式下起作用的并不是谈话本身,而是新的关系经验。这个新的关系体验,可以让病人内在的这个没有得到抱持的或者没有发展出来的部分得以跟上。病人就可以完成成长这个工作。
人们会问你是怎么做这件事的,或者你会做些什么?弗洛伊德在技术上面有一些规则。而在当代精神分析当中不存在这种所谓标准化的规则技巧。两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倾听我们的病人。不同的是我们听到了什么。比如说如果我们本来的信念,就是我们病人的动力,就是要阻抗、要防御,这是运用这种一人治疗的模式来思考。那么基于这种理念下,我们听到的、做到的就会和二人模式不同。如果我们的信念是病人的动力是为了成长,那我们所使用的模型是一个二人的模型。
科胡特会提到治疗关系中的“前缘”部分,看到病人做对的那些事情,而不是去看他们做错的。他引入了一个概念,叫做内省式的共情观察模式。内省和共情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倾听我们的病人的方式。有一种倾听病人的方式,是认为病人的动力来自于他们的阻抗和防御。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病人的动力是成长和发展,那么我们对他们的倾听就会不一样。当我们看到了一些不是正常发展而具有的攻击性和性驱力的时候, 科胡特认为这并不是创伤的带来的结果。在一人模型中,那些被认为是因为创伤,而不是因为正常的发展,并且阻抗也被视为是不正常的。而在二人模型中,当我们看到阻抗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个体的内在被禁止。阻抗是因为在那一刻,病人对分析师感觉不到安全感。我以前会认为我的病人是在逃避自己,不去面对自己。现在我视我的病人为挣扎着想要活下来。以前我所认为的自我破坏的行为。现在我视他们为急切的想要活下来的努力。其实也就是科胡特所谓的“前缘”。
我来举个例子,讲讲我是怎么样做到把自己的想法、观点去中心化的,就是不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而是把自己沉浸到了病人的视角当中。有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就是如果我们用病人的视角观点出发来倾听来理解,就直接把这种做法等同于我们同意病人的看法。但实际上一个人是可以在既不站在同意,也不站在不同意的立场上去理解一个病人的观点。
我之前和一个年轻的女研究生一起开展心理治疗工作。她当时身处一段虐待性的关系之中。有一天在她上学的路上,她的男朋友截住她,想跟她说话。这个女学生并不想要上课迟到,但是她的男朋友就求她,说自己很抑郁,希望她不要离开自己。她为男朋友感到难过,所以就跟他聊了起来,结果当天一整天的课程全部都没去上。在分析当中我们探索了她的信念,就是她认为如果自己去上课,而没有照顾好她的男朋友的话,那就等同于伤害了他。她认为照顾自己是很自私的。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位男朋友变得甚至要求更多、对她更有控制性。她不得不搬去一个女性朋友的家里面来学习上课。但是这个男朋友跟踪她,跟去了那个女性朋友的家里面,还因为这个来访者离开了自己而责备她。还有一次他还直接攻击了这位来访者,试图用枕头按住她的脸让她窒息。后来那个房主,也就是来访者的女性朋友,打了电话叫警察。在警察到达之前她的男朋友就逃走了,后来警察告诉她应该申请一个禁制令(法院会发布一张禁止令禁止这个人靠近),限制男朋友接近。在分析中,这个来访者发现她如果要去法院请求一张禁止令的话,那么她的男朋友就会感到很尴尬和生气。她想要男朋友不要骚扰她,可是她也不想让让男朋友难堪。再加上每一次男朋友爆怒发作之后都会感到很抱歉,在男朋友道歉的那些时候,她又会觉得跟男友非常的亲近。我感到非常的挫败,因为我们的分析没有帮助她从这段很糟糕的关系当中解脱出来。我开始感到担心,担心她会受伤,甚至会被杀掉。但她始终是感到无助,没法改变。我意识到我得要改变,设法改变我自己的思考方式。我必须要去中心化,我不能以我自己的想法为中心,我原先的想法是她是有受虐性的,是自我破坏的。我必须要共情性的,或者神入地沉浸到她的视角和她的体验当中去理解。我必须得要理解,站在她的视角去看,继续和这个男朋友在一起是怎么样帮到她自己的。所以站在这样的视角下,我探索了她和男友之间的连接带给她的体验。她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一个人生活,她的研究生学业也让她感到压力山大。她已经有一门课没有通过,正在那种延期待定的状态。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通过,能不能毕业。她感觉自己非常的脆弱。但是当她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她感觉会好一些,会感到有自信。我自己心里面想到的是一个很小的很无助的一个小孩子,很柔弱的一个孩子。但是当这个小孩子能够握住父亲强壮的手的时候,小孩自己也会感觉到自己很强大、坚不可摧。这样理解之后我就可以对她说了,我说,当然了,你会想要和男朋友和好,和他修复关系。当然了,你感觉到自己只有在和男朋友还连接着的情况下,你才能够活下来,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对你的虐待是你为了活下去一定要付的代价。她感觉自己得到了深深的理解。慢慢地,她就变得更加的自信。她现在就可以探索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对于舒适和安全的需要了。她开始去联络那些能够关怀她,不为她带来痛苦的人。在没有加以诠释的情况下,她内心的无意识内疚感形成的冲突也就浮现到了表面。她意识到自己的母亲一直以来都很依赖自己,一旦她开始独立起来了,母亲就会变得非常的焦虑。她发现自己的独立伤害了母亲。她有一个信念,就是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把日子过得比妈妈更好。当这些感受浮现到意识层面之后,她的内疚感就下降了,感觉自己更有力量了,于是她就去法院申请了一张禁止令。最终跟这个男朋友分手了。所以我当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理解她那些做法中的正确性,然后她自己就能想明白怎么样做更好了。
当我能够做到不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而是沉浸到来访者的想法当中去的时候,我又遇到另外一个来访者,另外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位来访者是一个38岁的律师。他在开始分析的时候,每一次开始时都会抱怨说早上见到他的时候我都不跟他说早上好。我知道我有和他说早上好,但是我当时想要继续和他的体验待在一起,我并不想要马上就去面质他形成的那个扭曲。所以每一天我都会有意地大声跟他说早上好。但是他还是继续在抱怨,他说你从来都不跟我说早上好,这简直要把我逼疯了。于是我有个冲动,想要告诉他,我跟你说早上好了,你没有听到吗?我觉得这肯定是一种阻抗,他有一些潜意识的需要,要瓦解、要不听到我的问候。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他,所以我在想,有没有一些他内心的主观上的真相,他看到的有关我的主观上的真相。那可能我也在以某种方式向他的这个体验做着贡献。我就问他,我没有跟你问候,没有说早上好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呢?他说这感觉太糟了,那让我想起来我自己小的时候,每天早上在父亲的房间门口等上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他起床出来。他的父亲是上夜班的,睡得也很晚,而且还伴有抑郁。父亲经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好几个小时。而当最终父亲出来的时候,他也表现不出任何迫切想要看到儿子的样子。小男孩渴望父亲眼中的光芒,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结果只得到失望。所以后来我就意识到了,因为我见他的时间是早上很早的时候,所以我在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完全的清醒。我确实是跟他说了早上好,但是我的这声问候当中眼里是没有光的,我的表情也是没有快乐,没有兴奋。我和他讨论这些,他告诉我他的感受不仅仅是失望,同时还感觉到羞耻。他相信父亲之所以会缺乏回应,是因为他自己的错,是他自己的失败。在我们探索理解了这些感受之后,他就可以开始听到我的问候,也开始可以探索我的视角了。现在他也会跟我说早上好。当我探索了我对他的反应有做出怎样的贡献,他也开始探索,他的过去对他的反应是怎样做出贡献的。
以这样的方式来倾听病人的模式,来探索病人的反应,改变了我对于病人迟到的看法。我自己的个人分析是从经典的精神分析的视角出发来做的。我几乎很少准时。无论我多么努力的想要准时到,但结果总是不可避免的迟到。我的分析师相信能够准时到分析现场,是自我发展成熟的标志。他认为我的迟到是一种退行,在自体心理学的术语里面叫做再度本能化(instinctuation)。他说我试图要来行使无所不能的全能控制。我当时的做法在他眼中是操纵性的,是在表达着我潜意识中的攻击性。他的诠释让我感到内疚,就好像我做错了事情。他的诠释也让我感到羞耻,就好像我身上有一些很糟的东西。当时我的分析师并不明白,我正在承受一种因夸张的责任感而带来的苦恼。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大人就教我的。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驱使,必须要把自己的一天塞得满满当当的。所以如果有某一个治疗我早到的话,我就会感觉到自己浪费了时间。因此我就害怕迟到,害怕浪费时间,而我的分析师又需要我准时到,我又很想要取悦他,于是我就在两者间挣扎。所以只有当我能够完完全全准时到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安全。
我现在把阻抗视为是为了活下去,而不是某一种病理情况。迟到并不是为了控制,不是我的分析师所想的那样的。迟到和我的分析师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是我自己对于混乱的感受的表达。我当时照顾着每一个人,但是却没有照顾自己。我很想要做一个好孩子,实现别人对我的期待。我认为活下去的条件就是要牺牲自己的需要,来适应别人的需要。而不幸的是我有太多的“主人”了。
这种思考方式也帮助我渡过了和另外一个病人之间的僵局。这个病人是一个32岁的职业女性,因为关系中的冲突,前来接受治疗。她爱上了两个男人,和两个男人在谈恋爱,这两个人都想要娶她。她在这两个男人之间摇摆不定,她仔细地检视了这两个男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的优点。经过一年的分析之后,她很尴尬的告诉我她的第三段恋爱关系。她和她的上司,一个已婚男人有一段婚外情。她下不了决心,因为她不了解自己的心。她感觉自己一定要按照别人所期待的那样去做。她从小受到的教育,也就变成了她的信念,即一定要按照别人的期待去做,不然的话就是很自私的。在这段分析的过程中,她总是准时到。当我们探索了也理解了她的潜意识,当然现在我就不会说潜意识了,而是程序性记忆之后。她开始感觉到自己是有权利拒绝别人的,也包括拒绝我,可以表达自己需要什么。她停止了自己和上司之间的婚外情,和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渐行渐远,然后和另一个越来越近。那段关系渐渐地绽放,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现在她开始在和我的治疗中迟到了。我当时还是用经典的模式在思考,也用了我的分析师对我的诠释,我把她的迟到视为对我的阻抗。我当时在思考这是不是对我有一些潜意识中的愤怒。她受到了我的诠释的伤害。她接受了我对她的诠释,然后就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生命的光彩。她变得很焦虑,我们的关系也开始变得疏远。迟到变得更加严重,有的时候她甚至不来了。我感觉我们进入了僵局。于是我就意识到,我一直都试图站在自己的视角,让她从我的视角出发去看,从来没有真的去理解她的体验。从一个共情的角度去理解,我意识到了她之所以总是准时到,是因为她感觉自己不得不遵守我的规则,一定要按照我的期待去行事。但是现在她正在成为自己,她正在发展出一种主体感。她的迟到是因为她正在探索她自己是谁,自己需要些什么,正在探索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实际上我的做法又让她经历了一次创伤,让她重新活在了小的时候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里。对父母,她必须得要自动化地顺从他们的期待,才能够持续的得到父母的支持。于是她假设,关系就应该是要这样子的。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是可以和我对质,对质我给她的诠释。她在过程当中尽全力地迎合我,因此就感觉好像被囚禁在了我们俩的关系当中,她所有其他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相信我要求她准时来做治疗,是为了维持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但我对她的诠释向她表现出了我对她的不认可,拉远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干扰了她来做自我定义、非线性化的这个过程,也就是干扰了她的独立。当我改变了自己的思路之后,我做的诠释也就不一样了。我告诉她,我现在能够理解她,并且欣赏她,而且她可以自己选择怎么样做是对自己最好的。她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想要继续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先完成工作,还是先来到我的办公室里面做治疗。不论她做哪个选择,我都会继续保持和她的连接。于是她的生命力又回来了。她变得更加的大胆,也更自信,我们的关系得到了修复,也变得更加的亲近。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晰地理解,她接受是什么样的教育,是怎么样长大的,她的父母是希望她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提升自己也好,都要满足父母对她的期待。她认为为了保持和其他人的连接,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照顾好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照顾好自己,她就必须得要退缩、退出人群和独处。为了能够好起来,她需要有一种新的关系上的体验,既可以做自己认为对自己最好的事情,同时还可以维系和我之间的关系。对她来说迟到是一种发展性的成就,而不是一个阻抗。这是一种她对自己新发展出来的自主感的表达。我要做的工作是先欣赏,然后才是去诠释她的这种新的自我发展,自我成长。在我这样做了之后,她就变得更强大,也更有自信,同时在外在的关系当中也变得更加的坚定有力。
我以前曾经相信洞察或者某种类型的诠释是很有必要的。我现在仍然认为一定的洞察和诠释是有必要的,但我后来的探索也发现:我们在行为上小小的改变,能够获得治疗上很大的益处。再举个例子,就是有个病人抱怨说自己感觉不到和我的连接。我探索他的感受,开始去理解有这么一个很疏远的分析师会为他带来多么大的挫败感。我对他的理解是根源于早期,他和父母之间很疏远关系。但他对我的抱怨还是在持续着。然后我就得到了一个关系性的分析师的督导。他提议我把我坐的这把椅子,搬的离沙发更近一点。我把椅子拉近了,病人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向我报告了一个梦,在梦里面,他在一个寄宿家庭。在家庭里面他在吃饭,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边,其他人都坐在他的两侧。他感觉跟那里的人很有连接。我没有对他的这个梦做任何的诠释,以后也没有再听到他抱怨我对他的疏远。通过坐的离他近一点,我为他提供了一个行为上的、非语言的关系上的重新体验,这比任何的诠释都更有力量。现在我相信在分析当中,很多的做法的有效性来自于行为的层面,而不是诠释。
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候选人正在接受经典精神分析的督导。他来找我做督导。他和一个年轻的女士工作两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分析进行的不错。病人能躺在躺椅上自由联想,定期来做治疗。而现在,病人会取消会谈,会坐起来,面对着分析师,还会批评分析师。分析师对病人的阻抗、愤怒做了很多的诠释,但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的督导跟他说放弃吧。督导说,来访者有太多付诸行动了,这个病人既不躺下,也不做自由联想,无法进行分析了。他说,你换一个人来接受督导吧。他暗示说如果你继续用这个案例来督导的话,这个候选人的身份是没有办法毕业的。但候选人对这个女士非常的关心,并不想要放弃他。他喜欢这个督导,但是同时认为我的观点可能和这个督导不一样,也许我有一种方法是可以帮到这个病人的。我确实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个分析师做得很好。我向他解释到这个女士在小的时候受到自己所信任的亲戚的虐待和猥亵。因此学会了活下来,就得要顺从别人对她的要求。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或者抗争过。所以,她的自我发展,她的自尊自主感,她的个体性都堵住了。在现在和分析师的分析过程中要经受的考验,就是如何把之前受阻的这些自我连接和成长重新恢复。她在两岁的时候经历的第一次反抗期,和青春期经历的第二次反抗期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而现在,她感觉到自己跟分析师的关系是很安全的,所以想要运用这段关系来发展自己的坚定感。在治疗当中,从顺从转变成不顺从并不是一种付诸行动。这是健康的,虽然看起来有点杂乱,但却是健康的自我坚定感的开端。这个分析师放松下来,也换了一个督导师。这个病人作为一个正常的反叛期青少年,对他来说是说得通的。他意识到无论是自己还是他的病人,在原先的工作当中都做的挺好的,虽然病人在抱怨,但其实是一种进展。他开始认真地倾听来访者的抱怨,但不再把来访者的抱怨视为是有意针对他的。他不再感觉到内疚,现在他也感觉可以自由、坚定地表达自己了。一开始他不能够对病人不来或者迟到的治疗收费,现在他也可以收费了,同时在收费的时候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在惩罚对方,或者因此而感到内疚。因为来访者现在在自己外面的生活当中,大步往前进。原本她在完成博士论文的进展当中受阻了,而现在她顺利地完成了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她同时也离开了一段虐待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很温暖很支持她,很有爱的男朋友。又经过了两年的分析,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之后,分析师就询问是不是准备好要结束分析了。这时候她又开始批评分析师,开始不来做治疗。分析师就坐在那里等着,同时还抱怨说:她至少可以打个电话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这段时间去做些别的事了。因为这个分析师正在接受培训,这个来访者钱不多,付的费也是比较低的。分析师感觉自己没有得到病人的欣赏,感觉自己被虐待了。我提议说病人正在用自己非语言的行为,沟通着自己小的时候被虐待的感觉。这个分析师感到又受伤又愤怒,所以我对他的解释并没有帮助他的感觉好起来。他过来做督导的时候,有一次对我吼叫了:“我恨她,我准备好和她终止分析了。”她持续的抱怨让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该怎么样理解他表现出来的暴怒和绝望。我的第一反应是他的反移情这么强烈,也许他需要进一步接受个人分析。我当时也觉得很有压力,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又不知道要做什么好,所以就同时觉得很内疚。我开始感觉到羞耻,好像我身为督导是个失败。病人触碰到了分析师的脆弱性,而分析师现在也触碰到了我的脆弱性,这个可以称之为平行关系。于是我就意识到了这个分析师在我这儿是能够感觉到安全感的,所以他在用病人对他施压的方式,同样地在向我施压。我说道,她给你施加了很多的压力,那是因为她在你这里有很多的安全感,所以你其实上工作做得很好。所以现在他就能放松了,于是我们就继续探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选项。我提议他可以做一个自我暴露,告诉来访者,如果她不来的话,打个电话会让治疗师更好做一点。他就这样做了,然后来访者就马上就向他道歉了,说很抱歉自己没有想到治疗师。她对治疗师说,一直以来你都对我非常的有耐心,同时病人带着非常饱满的情感,充满深情地告诉治疗师自己对治疗师的欣赏。
我以前受到的教导,同时我自己也相信,治疗师在分析当中做自我暴露是不好的,对分析没有什么好处。但我现在相信的是,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都要认真对待的。所以重点并不是要做自我暴露,还是不要做自我暴露,而是当你在做自我暴露或者没有在做自我暴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我再举一个做自我暴露之后发现非常有帮助的例子。这个病人是一个46岁的已婚的研究生。她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所以经常当她在抱怨的时候都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我发现她虽然很难,但是又很吸引人,很让人感到兴趣盎然。她实际上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治疗师。她当时正在做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而且她当时有一个6岁的女儿。她在童年的时候遭受过严重的虐待,在之前的4个分析师那里都没能修通,我是她的第5个分析师。她对我有很多的抱怨,比如说有些抱怨,就是说我很掉书袋(指卖弄才学),不真诚。我必须得时刻扩展自己,找到一种她认为很真诚,很真实的方式来和她一起工作。她很喜欢我对她讲一些我对她的理解,但是不喜欢我把现在发生的情况和她小时候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讲。比如说如果我提出她现在对丈夫的一些不开心,和小时候她对父亲的不开心是很像的,她就会反对。每一次当我记不住她以前曾经跟我讲过的一些过往的时候,她也会非常的受伤。她也抱怨,我没能帮到她化解自己对于那些曾经冒犯过她的人的纠缠。也就是说有人伤害了她,冒犯了她,她心里会一直萦绕着这些伤害,她抱怨我没有能够帮助她化解自己内心这种萦绕不散的纠缠。她希望我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她现在的生活当中去,教她怎么样来应对自己和女儿及丈夫之间的一些烦恼。在她的挫败感和失望之中,我经常感觉到内疚,感觉到自己能力不足。但是我后来又进一步的反思,认为我的反应,我的这种认为自己不足的反应,其实在潜意识的深处是与她的反应一致的, 她用一种潜意识的沟通,来让我体验性的理解了她对自己的感受,她认为自己不足。我没有告诉她我的感受,但是我想要很认真的对待她的感受,而是不防御自己。有一次她跟我说,她想要我更多的参与到她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告诉她我会尽力的,但我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说她抱怨我很有距离感、不够近。我跟她说,是的,我听其它的来访者也这样抱怨我。我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对她很有帮助。我在承认自己的局限性的同时,没有这么多的羞耻,没有这么多的防御,也并没有感觉很糟,这也就给了她支持的力量,让她可以直面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也不需要感觉到很多的羞耻感,或者感觉自己很糟。我对她的坚持不懈,同时很有决心地追求着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这种精神,非常的欣赏,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是以前当我还在用经典的精神分析模式工作的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在经典模式下,我会把她的不顺从,把她的坚定诠释为一种愤怒,一种攻击。我怀疑这是她和过去的那几位分析师之间发生的情况。但现在在她的抱怨当中,我能够听到的是一个很急切的孩子的声音,她既想要拥有着连接,同时也想要在不放弃自己的个体性的情况下拥有这份连接。我开始相信病人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而我的工作就是要搞明白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样通过对我的使用来实现她们所需要的和所想要的。有一天病人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说,她和她的毕业论文评审委员会当中的一个教师产生了一次很大的矛盾。她觉得那个男士不尊重她,因此她觉得非常的愤怒,甚至暴怒。她想要要求那个男士向她道歉。我当时深信不疑,觉得她是在想要破坏自己即将博士毕业这件事。她当时的感觉是自己的尊严受损。我任何提议她要顺从对方的提议都是在折损她的尊严。但她想要听我说说,想要我告诉她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起了我之前曾经跟她分享过的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我当时跟她说,在我的文化当中,人和人之间心里面怀有一些怨恨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现象。我跟她说在我的家庭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之间会好几天不说话。她说她所在的文化也差不多。她对我笑了一下,她说在她们家人之间可以好几年不说话。然后我告诉她我的妻子是在一种不同的文化下长大的。我的妻子是在天主教背景下抚养长大的,所以她受到的教导是当有人伤害了你,你要宽恕和原谅。我告诉她我花了好久才学会了原谅,但是当我学会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得到了很大的进展。她意识到了自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最高利益来行动的,同时在做的时候也不需要感觉自己妥协了什么。她向我解释道:在我的文化里面,如果有人侮辱了你的话,你就得要把她杀掉。现在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她跟身边亲近的人之间会有这么多争吵。她邀请这个老师出去吃了个饭,同时在那期间有了一次很有建设性的对话。同时也设法做到了协商,得到一种处理他俩之间的冲突的方式。
过去的行为模式是被编码在程序性记忆当中的,它们是自动化的,而且从来不会自动就消失了。但在治疗当中,来访者就有机会可以去实践一些新的存在方式,发展出一些新的做法。当我很自在的分享着我的个人经验的时候,我成为了她的一个榜样,一个她可以模仿的对象。我并没有告诉她要怎么做,选择仍然是她自己做的,但是她开始意识到了有一种新的建立关系的方式。我学到的一点就是通过仔细观察病人的情绪反应,我是可以得到情绪反应的指引的。治疗师经常想要知道的就是,你是怎么样知道的。他们想要提前就知道,说些什么或怎么说是对的,怎么做是对的。而我相信心理治疗是一种试错,尝试犯错。好的治疗师可以感觉自由地犯错,同时从自己犯的错当中学习汲取教训。犯错是不会让你惹上麻烦的,但是如果同一个错一再的犯,那确实会让你惹上麻烦。我还告诉治疗师,学习恰当的治疗技巧的来源,是你的病人。病人们知道要让自己好起来需要些什么。他们并不是在意识层面知道这些,但他们确实有自己的计划。我的目标就是在每一次治疗当中去发现,今天这个来访者需要怎么样使用我,好让他自己变得更好,变得好起来。当你对来访者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一些什么之后,仔细地观察来访者当时的直接的情感反应,是能够告诉你是否处于正确的轨道上的。比如说每一次当我说了一句话之后,我都会非常仔细地去观察。说完之后我的来访者直接的当下的情感上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他当下的情感反应是很有力量的,很强有力的,很有连接的,很有生命力,很有活力的。那这就说明我走在正轨上。比如说病人可能会说,不是的Shapiro,你没听明白,你一点都没明白嘛,你不懂我。这个回应是又大胆又有生命力的,这就说明无论我刚刚说的是什么,那就是病人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来访者当时的反应是迷惑焦虑,不连接的。那么我就知道我偏离正轨了,我需要换一种做法。比如说病人可能会说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吧,然后他的话里面没有生气,没有生机。我马上就知道我们陷入困难,我需要换一种做法。旧金山的Joseph Weiss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你明天去工作的时候就能够做。你可以非常仔细地观察你的来访者,去留意他们当下的直接的情绪反应。我指的不是他们字面上语言上说了什么,而是他们的情感。如果他们的反应是很大胆的,很强有力的,很有生命力的,那么不论你当时在做什么,都是你需要做的,不需要做什么改变。如果他的反应是非常平淡的或者焦虑的,或者是不连接的,压抑的,没有生命力的,那就说明你需要换一种做法。在那些时候,除了非常仔细地观察来访者在那一刻很直接的情绪反应之外,你并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事情。
我来举个例子。有一天我的来访者非常的不安,因为她的女儿放学回来之后向她讲,其它的小朋友不愿意跟她一起玩。这个来访者感到很内疚,她相信女儿之所以在社交上会有困难,是因为自己这个母亲做的不够好。她寻求我的帮助,希望我能够教她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母亲,而不是想要从我这里得到对她的理解。我模模糊糊地也感觉自己要负责任,就好像她在做母亲这件事情上的失败,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作为一个治疗师的失败。我从靠近她的位置上抽离出来,往后退了一点,对她做了一个镜映,我说,你担心你的女儿。她马上就生气了。她说你是很有同理心,但是你在用这番话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用某个技术,这个不适合我,我想从你这里得到的不是这种技术。在这个时候她已经非常地往后退了,我知道我遇到麻烦了。我意识到我让自己拉远了自己和她之间的距离,同时也知道这么做之后让我偏离了正轨。我也意识到她带给我的压力和她的女儿带给她的压力是一样的。我感觉自己有责任,要帮她处理好这些事情,就好像她感觉到自己有责任,要帮女儿处理好那件事情。现在我觉得可以真的好好想想到底是什么让她这么焦虑了。我对她说,你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你深信不疑,自己有一些有毒的东西。我继续说,任何靠近你的人都会受伤,而现在你女儿遇到的麻烦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你是有毒的。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说什么话,都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这个信念。她放松了下来。同时一边说一边脸上带着一个微笑,她说,有的时候得到一些诠释是会有点帮助的。现在她又鲜活起来了,我们又重新连接上了,我又回到正轨了。我当时并没有提前想好,话就脱口而出了,但事后想起来,我自己其实对于在关系中有毒,是有切身体验的,有我自己的经验的。她早年受虐的经历让她感觉自己是不可爱的,不值得被爱,而且一定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些什么,做错了什么,导致了她遭受这样的虐待。当她在我这里有这样类似的体验之后,我感觉到了之后,我把这些感觉用语言表达了出来。她感觉女儿的抱怨是对她的一种反应。她没有感觉到自己其实是可以信任女儿,相信女儿自己能够化解自己和朋友之间的问题的。相反她觉得自己一定要去帮助她。现在,她想要我来修理好她,帮助她。我对她的回应,向她说明了我对她的理解,并且也告诉了她,我并不认为我要把她修理好。我向她传递出了一种我相信她,而且她也需要相信自己的女儿。那时我承受住了她的情绪的风暴,并且继续的关心她,于是她开始可以相信,自己是可爱的,是值得被爱的。
所以每当你说了什么,或者对病人做了什么之后,仔细地观察他们当下直接的情绪反应。如果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大胆,强有力的,很有生命力的,那么就继续去做你之前已经在做的那些。但如果这个时候,病人给你的反应突然变得平淡起来了,变得不那么有连接感了、焦虑了、阻抗了,那么就可以去做任何改变尝试,只要这个尝试和你之前做的不一样就可以。
作者介绍:

Sanford Shapiro, M.D
自体心理学取向精神分析师
圣地亚哥精神分析学会前主席
当代精神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杰出终身会员
国际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学会理事
《国际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期刊》编委
(本文内容为厦门朴生心理原创,版权归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所有。转载请联系15859242450,并注明出处。)
预约咨询请添加助理微信: